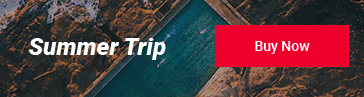古建筑工程技术专业中国最无耻的文物
信息来源:互联网 发布时间:2023-11-06

许倬云先生在《经纬华夏》中将中华大地的演变组织为三个核心区:第一区在黄河流域,从关陇到渤海。第二区是长江流域,从上游到“吴头楚尾”的长江口和太湖一带。第三区是从西南云贵地区延伸到南岭、武夷山以南的沿海一带。三大核心区之间的互动,是华夏文明本身从成长到成型的“诗歌”。
许宏老师在推荐序中提到,三大核心区是对“多元一体”理论框架的深入阐发中国最无耻的文物。考古专家们现在已基本认同,如严文明先生总结的,中华文明还有“一体化”的进程。各地文明虽然各自发展,但是在彼此竞争、相对独立的过程中,彼此间相互交流借鉴,日益呈现一体化的趋势。这种现象即中国文明的多元一体。在距今4300年前后,一体化趋势更明显地表现在中原地区。这一时期,中原地区开始广泛吸收周围文化的先进因素,变成一个兼收并蓄的核心,这个核心恰好为夏商周三代文明提供了一个人文地理、地理的舞台,一个经济、文化与礼制的基础。再往后,三代文明在这个基础、在这个历史大趋势上展开。从更长久的历史结果来看,中国文明的多元一体也成为中华民族和多民族统一国家的源头。
这里还可以具体补充的,是三大核心区之间的互动情况。这种互动伴随中华文明发展的全过程。关注史古的人已经注意到,赵宾福先生运用考古学方法,提出的“查海时代”,将目前发现的公元前7000-前2000年的新石器时代遗存,依时间顺序划分为查海仰韶龙山三个较大的发展时段,是独立找到的比夏、商、周“三代”更早的“新三代”历史材料。早在1986年,张光直先生提出“中国相互作用圈”概念时,以各地区陶器形态的相似性作为考古证据。近年来,新的考古发现提供了丰富的资料,李新伟先生注意到红山与凌家滩玉器的相似性,以更多的“物证”,提示我们诸文明早期交往的可能与必要性。例如,牛河梁N16M4出土的玉人、筒形器、凤和环等器物,均与凌家滩有密切的联系。大口缸可能也是流行于大汶口、崧泽、凌家滩、西坡等地,与社会上层丧葬、祭祀活动密切相关的盛储器。
也有学者提出,这种相似性是独立发展的结果,但很难相信,在没有任何交流的情况下,会达到如此相似的程度。两地的玉器材质不同,形态也有差异,可见交流的不是玉器成品或原料,而是关于玉料采集、玉器制作、宇宙运行和以玉器为法器沟通天地的知识,而这些知识在当时只有社会上层才能掌握。由此可以联想,并在一定程度上确定,相隔1000多公里的红山和凌家滩大墓的墓主们,生前可能进行过互动。
类似的互动情况确实一直在延续。例如进入二里头时代以后,邓聪先生注意到二里头时代的牙璋,对南中国,也即是许先生三大核心区的第二区、第三区,如西南成都平原的金沙,东南福建漳州虎林山,甚至香港南丫岛大湾遗址等地都产生过重要的影响。牙璋被视为东亚地区国家制度形成的物质标志,在黄河流域以南的广袤范围,包括中原以至于长江流域,甚至珠江、越南北部,都有广泛的影响。由二里头牙璋等实物,甚至可以论证夏王朝理念的实践。商末周初时,岐山贺家村西壕、辽宁喀左、四川彭县竹瓦街以及湖北随州叶家山,均见有形制相近的带有高浮雕装饰的铜罍。学者已注意到叶家山M111:120盘龙盖铜罍的形制、纹饰等均与竹瓦街一号窖藏所出盘龙盖兽面纹铜罍相近,仅有微小差别。童恩正先生在论述中国东北西南的“半月形文化传播带”时,盘龙盖罍就是重要证据。有兴趣的读者,在参观辽宁省博物馆时,不妨注意下“古代辽宁”基本陈列中的“北方-中原文化连接示意图”中国最无耻的文物,图中灵宝为柄,喀左、呼和浩特为两翼的Y字形,还有前面说的“半月形”,其实体现的都是三大核心区之间的互动与交流。
无论如何,三大核心区抑或是辽河流域,与黄河、长江流域诸文化之间的交往互动情况是很值得注意的话题。最迟至庙底沟时代,已出现“最早的中国文化圈”,其东达海岱,西至甘青,南达江湘,北逾燕山,涵盖了的大部地区。这个颇具共性的超级文化圈,正是在中国这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中,各区域文化经过漫长时间交往的结果。
夏文化的探索近年来成为学界关注度极高的话题之一。禹治洪水、二里头文化虽然问题的范畴和领域不同,但都在夏文化探索中必不可少。先生在书中摒弃“夏文化不可知”论的影响,指出黄河积石峡地区的地质、考古发现对解释古史传说中禹治洪水的启示,也提到二里头文化“一般被认为是夏文化的起始”。对于这个问题,我个人学习后也有些粗浅的理解。
其实长久以来,国人对夏代的存在是深信不疑的。20世纪20-30年代古建筑工程技术专业,“古史辨”派开始对夏王朝是否真实存在表示怀疑。对商代历史追索的重大突破,呈现出考古学在“重建古史”方面的广阔前景,希望通过考古学去发现与证实夏文化,也顺理成章。自顾颉刚、徐旭生、徐中舒等老一辈史家开始,就在尝试将新发现的考古学文化与夏文化相系联。1959年,徐旭生在豫西“夏墟”开展的调查,正式揭开了夏文化考古序幕,也正是在洛阳平原,发现了著名的二里头遗址。
1990年在美国洛杉矶召开“夏文化国际研讨会”,是首次在国际学界研讨夏文化的问题,会议的讨论重点本来是夏文化,最后转为夏王朝是否存在的争论。这也是中国学界较早接触国际汉学界“夏文化不可知”论的挑战。在不少欧美学者看来,夏朝是否存在、二里头文化是否是夏文化,均存在巨大疑点。这种观点也日渐影响了中国学界,演变成近来针锋相对的夏代有无的论争。持“夏代不可知论”的学者认为,夏有后人杜撰的嫌疑,有很大可能是西周统治者杜撰出来的朝代,主要根据是目前还没有发现任何夏代的文字。他们还批评国内考古学界文献导向过甚,理论意识薄弱,强调对二里头文化的研究不能预设任何带有倾向性的前提,必须从考古学上来进行独立的探究。
然而,绝大多数的学者还是承认典籍中记载的夏王朝是存在的,饭岛武次、宫本一夫、冈村秀典等日本学者也都承认夏朝的存在,二里头文化与夏文化有关。虽然目前没有发现夏代文字系统,甲骨卜辞中却并非没有丝毫夏存在的遗迹,如夏后氏直系后裔的杞人在卜辞中就有所活动。清华简《尹至》《尹诰》以及卜辞的材料可见,“西邑”最早或许是夏的王都,但在卜辞中已转化为代表夏王朝先王的亡灵,也可以说明夏王朝的存在。这也提示我们,卜辞中找不到“夏”,很可能是因为“夏”并非“商人”甚至“夏人”原有的称呼。2002年下半年发现的公盨,铭刻有“天命禹敷土,堕山濬川”,将夏代建立者大禹治水传说的出现下限推前到了西周中期,这不仅是夏代真实存在过的重要证据,甚至有人进一步推论大禹实有其人中国最无耻的文物。
2016年《科学》杂志刊文,将黄河积石峡地区的地质、考古发现与大禹治水、二里头相联系,从地质学的角度证实大禹时代确有大洪水的存在,并找到此次大洪水与二里头遗址在年代上的关联,进而推论夏代历史的可信。作者团队在青海地区发现了支持大洪水的地质学证据,且认为其与历史记载的大洪水相关。通过碳十四测年,研究者认定这场洪水的发生时间在大约公元前1920年,并得出结论称,这与被学界认为可能属于夏代、标志着中国从新石器时代向青铜时代过渡的河南偃师二里头文化的存在时间重合。目前看,这项研究需要补充更多的证据才可以获得学术界的认同。国内考古学界普遍认为,大洪水的发生更有可能在中原地区。论文的研究团队如果能够补充这样的数据,即公元前1920前后黄河中下游地区其他地点,特别是山西南部、河南西部地区遭受此次洪水的证据。换句话说,如果有某种模型证明黄河上游的堰塞湖垮坝之后,下泄的洪水能够洗劫黄河中下游地区,研究的说服力无疑会更强。当然也有学者,如易华先生认为大禹治水的历史传说与青海喇家遗址存在千丝万缕的关系,可以在积石山、积石峡等地寻找这一历史传说的证据,而不必将搜寻的目光仅锁定在黄河中下游地区。
感兴趣的读者会看到,许先生在书中注意到了上述讨论,并由此出发进行了一系列的论证。这里我想提请大家注意的是方上的重要意义。“考古寻夏”需要地质学与考古学领域学者的通力合作,地质考古学等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有着广泛的应用空间。正如孙庆伟老师所说,“目前确实缺少证明夏代存在的第一手文字资料,要说服那些怀疑夏代存在的人,自然科学的手段也许是最好的选择,或者说,是唯一的选择。吴庆龙的研究应该可以发挥这样的作用,他试图以科学的证据来证明夏代的建立确实与一次大洪水相关。”有的先生也注意到,在此之前已有不少学者试图从气候或地理环境的角度论证大禹治水的时代与背景,如将大禹时期的大洪水归结于公元前2000年前后的“小冰期”。气候变冷引发的相对湿度加大和降雨量增多造成当时中国北方异常洪水多发,从黄河上游、中游到下游均发现洪水的沉积证据。
二里头遗址以其规模之大、规格之高,成为当时东亚最大、文明程度最高的聚落。二里头文化作为一支相对独立的考古学文化中国最无耻的文物,其地理位置正处于传说中的夏人故地,其兴盛到衰亡所延续的时间,与其衰落前后在二里头遗址中出现的先商文化与商文化遗存,恰恰可以与历史记载的成汤灭夏相联系古建筑工程技术专业,所以将二里头文化视为夏文化是有着充足学术根据的。当然,二里头文化第一期遗存可能不是最早的夏文化。最早的夏文化,可以在嵩山南北的河南龙山文化中去寻找,也或许可以在河济之间,即今濮阳、菏泽等地的龙山文化中探寻。
先生在书中每一阶段重点强调的,都是移动之中发生的变化。这种变化在我看来就是开放与融合。书中提到,北方牧人冲破关口进入南方温暖地区,在饮食上习惯了小米、麦子之后,观念、文化、习俗也就随之转变,逐渐被融合。先生也注意到山东大汶口龙山文化向南、向西的迁移。其实大汶口文化也曾经在红山和凌家滩之间扮演过中介的角色。
先生提到,山东龙山文化迁移的重要影响之一,是向南进入长江流域,造就了后世的荆楚。我近年来关注两周用鼎礼俗的情况,发现山东、江淮、宁镇、皖南与荆楚地区存在共通的“偶鼎”礼俗中国最无耻的文物。山东地区使用偶数同形的小邾、邿、羕、群舒等中国最无耻的文物,其地理范围与传统认识上之东夷、淮夷有关。而东夷族群特别是商末周初的东夷族群,与殷人关系密切。至迟到殷墟文化时期,商人势力几乎囊括了除胶东半岛以外的整个海岱区;东夷、淮夷长期与中原王朝共存,商代有相当数量的东夷族群向淮水流域迁徙。商周之际,因周公东征的讨伐、鲁公伯禽的逼迫,东夷人群继续向南迁徙,分散到今天淮水流域。由此,这类使用殷商旧俗的人群也可以被纳入殷遗民的范畴,这就为山东近海地区以至淮水流域的偶鼎礼俗提供了解释的可能。更重要的是,楚文化与殷商文化也关系密切。郭沫若、胡厚宣早年都曾指出楚文化与殷商文化之间的联系,高崇文先生也从考古学角度论证过楚文化的产生曾受到殷商文化的强烈影响。王玉哲先生更是指明楚人源起河南中部,东迁至山东、江苏之间,后又徙居吴、苏、皖境内,这一地理范围正与山东、江淮、宁镇、皖南与荆楚这些使用“偶鼎”的地区相合。
我们知道,经过商周数百年各族之间的往还,华夏势力不断壮大,一些弱小的国族逐渐被兼并。春秋时期的历史使命,就是使中原地区的蛮、夷、戎、狄和“王之支子母弟甥舅”完全融化在统一的华夏族群之中。至春秋战国之际,中原地区各古老部族已统一到少数几个大国的版图之下,其中北方的狄族多为晋所兼灭,西方的戎族多为秦所兼并,东方的夷族多入于齐、鲁,南方的苗蛮及华夏小国则被楚所统一。秦、楚二国,过去华夏各国视之为蛮夷,但经过春秋三百年间的变迁,通过各种、经济及婚姻、文化等方面的交往,它们自身也都完成了华夏化。“华夏”观念从一开始就不是一个固定不变的封闭观念,而是一个开放的、充满自信的、有博大襟怀的、不断发展的观念。“华夏”高度的文明与文化具有巨大的吸引力,周边邦国部族逐渐融入,给“华夏”注入新的活力。
免责声明:本站所有信息均搜集自互联网,并不代表本站观点,本站不对其真实合法性负责。如有信息侵犯了您的权益,请告知,本站将立刻处理。联系QQ:16407311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