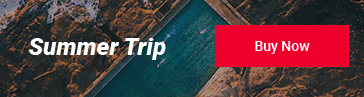文化遗产包括哪些敦煌历史文化名城
信息来源:互联网 发布时间:2023-12-14

西汉建元二年,张骞出使西域,奉武帝命向西方大月氏寻求合作,以夹攻在北方作乱的匈奴。此一行便是十三年,张骞历尽万般艰险方得返回长安,虽然未能带来汉武帝想要的盟友,却带回了空前详尽的西域见闻,并由此打破了中原与西域之间的交流障壁。在《史记》载录的张骞出使报告中,录有一句:“始月氏居敦煌、祁连间。”这是首次提到“敦煌”这个地名。后来汉武帝平定河西匈奴后,便在河西设置酒泉、张掖、敦煌、武威四郡。“敦煌”这个名字便是从此进入了中国的历史。
千百年间,“敦煌”这一地名在历代流传沿用,广为人知。但这“敦煌”二字的词源却早已无人知晓了。古人曾用汉语字意来解释这个名字,东汉应劭在《汉书》中说:“敦,大也。煌,盛也敦煌历史文化名城。”唐人李吉甫则沿用此说,言:“敦,大也。以其广开西域,故以盛名。”但敦煌这个名字,是张骞出使西域带回的,其发源应该要早于汉武帝立郡命名,所以这个汉语解释固然好听,却也难令人信服。
今日学者大多主张“敦煌”是当时某种少数民族语言的音译。而对其词义的具体解释仍是众说纷纭:有学者认为敦煌是吐火罗语中,自称族名“吐火罗(Tokhara)”的音译;或有说其源自当时居于此处的戎狄语言,意为绵亘的大山;也有推测敦煌源自羌语,为“朵航”之音译,意为“诵经地”或“诵经处”,凡此等等。
无论如何,自汉始,这片地处河西走廊西端,背靠三危山的临河绿洲,便以敦煌的名字频见于史书之中了。西汉建郡之后,将敦煌视为朝廷经营西域的支点,遂在此大加建设。汉将赵破奴在今党河西岸修筑了最早的敦煌城塞。武帝又命令在敦煌城西建造玉门关、阳关,两关之间筑长城相连,将敦煌地区打造成了兵农一体的边关城塞。此后,通过迁徙移民、屯田、畅通西域商路等一系列措施,敦煌境内不仅逐渐富足,而且商业交流繁盛,呈现出太平繁华的景象。
在敦煌建郡后的数百年里,中原地区经历两汉更替、三国争雄、南北朝政权交迭,这处镇守河西走廊的战略要地自然也免不了数度易主。但值得注意的是,无论统治者如何更替,相对于中原腹地的战乱频仍,敦煌却往往能保持相对的安定,在中央政权稳定后,它也能更迅速地恢复到往日的繁荣。这与敦煌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密不可分:
一方面,它偏于西隅,在中原内乱时能够远离战火的侵扰,保持相对稳定河西明珠—敦煌的立郡与兴盛的发展环境;另一方面,它地处西域交通要道,往来商贾皆由此经过,商业文化发展不致断绝。此外,中央政权也往往仰赖敦煌的地理位置来巩固对西域诸番的控制,对此地大加建设。
自然而然地,敦煌便能在战乱时期吸引大量的中原人士前来避难,其中也不乏文人世家望族,他们不仅在敦煌扎根立足,还开堂讲学,带来了繁荣的中原文化。例如东汉时期著名的硕儒张奂、张芝父子,便是敦煌张氏的后裔。今日我们从敦煌遗书中看到的璀璨文化,也便是在这样的环境中打下了基础。
而在另一个角度上,自而来的商旅也为敦煌地区的宗教转播提供了便利。尤其印度与西域的佛教高僧,如欲到中原传法,则必经敦煌。据《高僧传》记载,3世纪中叶,高僧竺高座就曾在敦煌活动,并收竺法护为徒。竺法护是敦煌佛教史中的关键人物文化遗产包括哪些,他通晓36国语言,善译佛经,且广收僧徒,布道说法。这为敦煌日后开凿莫高窟,发展为绵延千年的佛教圣地埋下了种子。
传说前秦建元二年,一位名叫沙门乐僔的禅僧途径敦煌地界。他在三危山间持杖穿行时,忽然抬头见到山顶有辉灿金光笼罩,恍惚间如有无数金佛出现在山中。乐僔和尚大受震撼,将三危山视作有佛缘的宝地,于是就地宣扬佛法,在鸣沙山麓开凿了第一处佛窟。千年千佛莫高窟,就是在这样的机缘巧合下揭开了历史的帷幕。
这段传奇的经历,存录于莫高窟《李克让修莫高窟佛龛碑》之上,此碑曾立于今332号窟内,但十年被俄人折断,今仅存残碑一方。所幸有徐松、罗振玉等学者辑录原碑文,我们才能看到这段文字记载。此碑立碑纪年“维大周圣历元年岁次戊戌伍月庚申朔拾四日癸酉敬造”,是现存关于莫高窟修建历史最早的一段史料,因此学界也大多采信此碑中的说法。
乐僔和尚开窟后约十余年,法良禅僧从东方远游而来,在乐僔窟旁开凿了山中佛光—莫高窟的开凿与鼎盛第二窟。可惜最早开凿的这两窟如今已无迹可寻了。此后自十六国晚期的北凉,至南北朝时的北魏、西魏、北周,敦煌鸣沙山的佛窟逐渐增扩,遂形成了早期的莫高窟佛教艺术。
这一时期的莫高窟,很好地表现出了当时敦煌地区西域文化与中原文化交融的风貌。在十六国时期的佛窟内,人物冠服皆明显地传自西域与波斯,绘画艺术也有着与当时中原地区迥异的风格。
但是同时,其中也能看到中原地区儒家文化审美对莫高窟艺术的筛选与改造,尤其北魏孝文帝推行汉化,至北魏末期,汉化之风也渐进地传至西陲。当时的东阳王元荣自洛阳至当时敦煌所在的瓜州出任刺史,也将中原的艺术风格传至此地,他引领了莫高窟第二次开窟造像的热潮,也使得中原地区“褒衣博带”的服饰风格,出现在莫高窟的造像与壁画之上。
隋唐两朝都是疆域开阔的统一王朝,西疆相对安定,且在帝王的倡导下,隋唐时期的崇佛之风盛行,莫高窟在这样的环境下迎来了发展的鼎盛时期。
隋代国祚虽仅三十余年,但炀帝在位期间解决了西域吐谷浑和西突厥的问题,畅通商路,使敦煌地区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加之隋朝尊佛教为国教,两代帝王对佛教的倡导,使敦煌地区的佛教发展更为鼎盛。如仁寿元年(601年),隋文帝诏令天下各州建舍利塔,也在莫高窟(时称崇教寺)建了佛塔用以存放释迦舍利。炀帝更曾亲自巡幸河西,派人到敦煌修寺建塔。如此热潮之下,莫高窟在三十余年间新开佛窟九十余处,其鼎盛可称前无古人。
唐代国力强盛,对西域的经营也十分重视,敦煌不仅是维持西域控制权的重要支点,也是丝绸之路上沟通西方世界的一大枢纽,因此经济与文化在当时极为繁荣。尤其武则天治时,善用佛教维持自己的统治,遂推行崇佛,令天下普建大云寺,敦煌的佛教文化也在这番浪潮中盛极一时。当时的敦煌寺院、佛堂林立,且在当地颇有影响力的名门望族也十分支持佛教事业,莫高窟无论是规模还是艺术水平都达到了顶峰。
这一时期的莫高窟造像、壁画都展现出了鲜明的时代风貌。除了具有雍容端庄的造像风格外,唐代还塑造有数尊巨大的佛像,如延载二年兴造的33米大佛,是莫高窟最大的佛像,今称“北大像”,与之相对应的还有开元九年前后兴造的南大像,高26米。这类巨大雄浑的造像,是盛唐气象最集中的体现。除造像以外,这一时期窟内的壁画也是异彩纷呈。如隋代藻井中开始出现的“三兔共耳”图案,又如唐代的“飞天”,都是莫高窟最具代表性的壁画形象,至今仍被世人所熟知。
“三兔共耳”最早见于莫高窟,但在欧洲、埃及等不同文化和宗教中都频频出镜,其起源目前仍无定论。
敦煌在唐朝治下的盛况,随着“安史之乱”而走向衰落。贞元二年(786年),沙洲在吐蕃的包围下困守十年后,因粮草耗竭而与吐蕃议和,史称“番和”,自此吐蕃统治敦煌地区六十余年。吐蕃是一个信奉佛教的民族,因此其治下的敦煌佛教发展丝毫不输隋唐,莫高窟内开窟、开寺都极为频繁,今日仍能看到不少具有吐蕃风格的造像、壁画,可见其佛教建设规模有增无减。但是与繁盛的佛事相对比,当地汉民在吐蕃的统治下生活却颇艰辛,吐蕃统治者推行吐蕃文字、历法,逼迫汉人编发易服的行为频频激起民间反抗。
唐大中二年(848年),沙洲豪族张议潮率军驱逐了吐蕃守将,使敦煌重归唐朝。张议潮出任节度使,统领河西归义军,敦煌从此进入了归义军时期。敦煌的归义军统治历经张氏、曹氏两个家族,前后近二百年,横跨了唐末、五代至宋初,是在中国历史中颇为特别的一个政权。在这一时期里,除了唐祚告终之际张承奉曾短暂宣告独立外,历任节度使都奉中原王朝为正朔。但事实上,唐、宋等中原王朝敦煌历史文化名城,在当时都处于内忧外患的境地中,根本无瑕顾及西陲的统治,因此归义军中的节度使就成了敦煌实际上的统治者,他们在回鹘、辽金等外族的环伺下守河西百余年,实甚难得。
莫高窟156窟 归义军节度使张议潮统军出行图(局部)张议潮晚年留质长安直至去世,以表明忠心无二
归义军时期,敦煌远离中原战乱,在西域各族之间也基本能稳定立足,因而经过了一段相对稳定发展的时期。归义军两代节度使张氏、曹氏家族,都对治下的少数民族持包容态度,也能够妥善处理和当地佛僧的关系,敦煌地区的佛教和莫高窟开凿事业仍在稳定的发展。在特殊的时代背景下,此期的莫高窟艺术又有了与前代不同的新风,更加写实与世俗化。例如,佛窟内开始为当时的佛教高僧塑像,著名的高僧洪禅定像即为代表;又如佛窟内壁画上更多地出现供养人像,多为供养窟内佛像的世家望族所绘,典例如节度使张议潮夫妇、曹议金夫妇的出行像,此类画像充分体现出了当地豪门望族在归义军时期所掌握的势力远胜此前任何一朝。
值得注意的是,支撑起敦煌学大半的莫高窟藏经洞,据研究也应是在这一时期封存。藏经洞原是莫高窟第16窟侧的一个耳室敦煌历史文化名城,后被寺内僧人用作密室,将一批经卷、画作、社会文书、香炉、法铎等经籍文物统统收入其中。而后,僧人们又用泥砖封闭洞口,在封闭后的墙壁上绘制了一幅精美的壁画,将洞口巧妙地隐藏了起来,数百年间竟无一人发觉。在佛窟中设置如此精妙的一处密室,必然是有特殊原因的,因此关于此处藏经洞的历史与封存经过,也是当今学术研究的热点之一。
据调查,藏经洞中文献的最晚纪年是咸平五年(1002年)的《施入记》,因而可认为藏经洞的封闭不应距此纪年太远。而关于设置藏经洞并封藏的原因,目前仍有着很多种解读。有学者认为藏经洞封存应在归义军时代末期,当时归义军内衰落,回鹘势力复起,继而又传来信奉伊斯兰教的黑汗王朝灭掉于阗佛教王国的消息,担忧莫高窟佛教存续的僧人,遂将这批经书典籍封存起来,并做了细致的掩饰,以期躲过可能到来的伊斯兰势力(或西夏人)。除此以外,也有“书库改造” 、“佛教供养法物”等数种观点,不一而足。
近年来,也有学者依照当时的历史环境与文化氛围,提出了颇有说服力的新观点,即曹氏归义军在与邻近的辽朝互通使者的过程中,接收到了盛行于辽的末法。“末法”是佛教中的一个概念,当末法到来时,佛、法、僧三宝将灭,众生不求佛法,僧尼亦不种善根。莫高窟的僧人们,亦有可能在对末法将至的担忧中,封藏了这处存有佛教经书典籍的洞窟,以期末法到来时能够度人。
归义军政权消亡后,敦煌历西夏、元、明、清数百年统治,再没能回到隋唐时期的那般鼎盛,已是走在了日暮西山的道路上。
西夏、蒙元都是尊崇佛教的政权,在他们统治下的敦煌虽然不及汉唐那般繁盛,但当地的佛教文化传统得以存续,莫高窟的营造也遂不致断绝于此。西夏与元两朝都在莫高窟留有不少具有时代风格的造像与壁画,与之前中原政权统治下的佛窟相比,这一时期的佛窟艺术有着更为鲜明的少数民族特色,一些石窟中也出现了此前不见的密宗题材壁画,其中展现出狰狞刚烈、色彩浓艳的藏传佛教艺术风格,与含蓄的中原文化迥异。
莫高窟的艺术脉络真正告绝于明代。当时的敦煌地区边患难绝,瓦剌等少数民族对敦煌地区的袭扰十分频繁,明朝政府对西域的几度经营也不见成效,遂在几次徙民入关后,完全退守至敦煌东方的嘉峪关内,对敦煌彻底关上了中原的大门。此后的敦煌几乎已没有汉人居住,占据此地的吐鲁番也无意经营,敦煌与莫高窟就此堕入黑暗。
至清代时,历康雍乾三代西征、徙民、经营耕作,敦煌逐渐重归于中原王朝的统治之下,社会经济也开始复苏。但是,曾经在敦煌延续千年的文化传统已无法接续,人们虽然在此重建了新文化,但其高度已经无法与前代相提并论。清代对莫高窟的一些修葺整顿,甚至可以被视作对莫高窟原貌的破坏。
王道士本名王圆箓,湖北麻城人,原在肃州巡防营为兵勇,离军后受戒做了道士。他一路行游化缘文化遗产包括哪些,途径莫高窟时,认定此地有道缘,于是就地打扫出几洞佛窟,经营起了一座道观。王道士在此地供奉香火,收受布施,兼又四处布道。清末时的敦煌民间,以务农的移民居多,王道士又能说会道,此番传教竟然小有名气,香火颇盛。有了一些积蓄敦煌历史文化名城,他便思索在莫高窟修缮自己的道观,除了将一些佛像改作道教灵官之外,也清理一些洞窟内的积沙,打通洞窟间的隔墙,便于通行。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一名受雇于王道士的伙计,在休息时偶然发现一幅壁画后面可能有空洞。于是当晚,王道士便带着这名伙计打破了墙壁,见到了里面那个用泥块封着的密室和里面堆叠成山的经卷典籍。封存近900年的藏经洞,就这样重见天光了。
王道士虽然文化不高,也深知洞中的绢画经卷是稀罕的古物,于是他从中挑选一些品相精美的,进献给自己所能接触到的“达官贵人”,期望换些银钱更好地进行自己修缮道观的事业。而这些人中竟无一识得这批古卷的真正价值,甚至安肃道道台廷栋觉得里面的字不如自己写的好。直到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敦煌县令汪宗瀚把从王道士那里收来《水月观音像》和《大般涅槃经》转送给甘肃学台叶炽昌,叶炽昌是当时著名的金石学家,识得这批东西是唐物,建议将藏经洞珍宝运到省城兰州妥善保管。这本是挽救藏经洞内珍宝的一次机会,但当地官员却以筹集不到七辆大车和五六千两运费为由置之不理。王道士最终仅收到了一张调查清单,和一道“照旧封存”的指令。
后人谈论这段历史的时候,往往痛惜于王道士的愚昧和贪婪。但回首细看事情的来龙去脉,王道士是恐怕只是个站在历史路口上的小人物,在滚滚而来的时代车轮面前,他无论作何选择,都改变不了这批珍宝遭劫的结局。
经此一番折腾,莫高窟发现藏经洞的事情,很快传到了当时在新疆地区寻宝的外国探险家和考古学者耳中。第一个找上门来的外国人,是英籍匈牙利探险家,马尔克·奥莱尔·斯坦因。1907年斯坦因到达敦煌,但他等了足足两个月,才终于见到外出化缘归来的王道士。王道士见到这个上门求宝的洋人,心里也曾有过一分忌惮,最初不肯出示。但斯坦因受敦煌壁画《唐僧取经图》的启发,又利用了王道士对信仰的执著,自比为西天取经的玄奘,加之身边带路向导蒋孝琬在旁游说,斯坦因轻易地取得了王道士的信任,最终用少量银钱就换回了24箱写本和5箱绘画、刺绣等艺术品。他的这些“探险成果”,后来入藏于大英博物馆、印度事务部图书馆、印度新德里中亚古物博物馆。
伯希和将所得运抵巴黎后,才与中国学者交流了这批文物。罗振玉、蒋伯斧、王仁俊等著名学者至此方知敦煌藏经洞之事,遂立即上书学部,督促清廷重视此事,并将剩余文物清点后押至京师。但清廷连这最后的机会也没有抓稳。剩余的经卷古物里,先是王道士私藏了一批;押运的官吏渎职,运输途中又遗失一批;到了京师,负责此事的新疆巡抚何彦升伙同亲友从中偷窃若干,又将剩余经卷撕开抵充8000之数,方才交给学部,入藏京师图书馆。
这剩余未到京师的经卷古籍,被王道士和中饱私囊的官员,又卖给了二次来华的斯坦因、日本人、人,更有不少就此流散,不知所终了。
除了藏经洞内的文物,莫高窟的造像壁画也难逃劫难。满清垮台后,敦煌为政府所统辖,但刚成立的政府尚无瑕顾及西陲边关,莫高窟内的壁画、文物更是饱经摧残。
1920年,一伙沙俄从苏联溃逃至甘肃境内敦煌历史文化名城,数百名白俄士兵竟在莫高窟内生活了半年多,导致许多壁画被污染损坏,塑像也多有损毁,此为一劫。
1923年,美国考古学家兰登·华尔纳来到敦煌,他仍是用几十两银钱就成功贿赂了王道士,在莫高窟内破坏性地剥去了20多幅壁画,还劫走两尊彩塑。在莫高窟经历了如此之多的劫难之后,华尔纳此次的灾难性的掠夺终于激起了国内社会各界的反对。1925年,当他再次来敦煌企图剥取壁画时,迫于众人的强烈谴责而告败。1940年,敦煌县保安班派10多人驻守莫高窟,外国人在敦煌的肆意掠夺,至此才勉强算是画上了句号。
“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陈寅恪在为陈垣《敦煌劫余录》作序时,引用了这样一句评语文化遗产包括哪些,回首观之,诚然如是也。但如果将目光放得更宽阔些,在千年的尺度上回顾敦煌的历史浮沉,又不禁令人对它心生敬意。
它生于盛世,见证了河西地区的势力争锋与王朝更迭;见证了四海商旅和着驼铃声的仆仆风尘;也见证了莫高窟千百年间林立的佛窟与造像。它曾经繁荣,曾经衰颓,也曾经历遭劫难。然而时至如今,当你踏上敦煌的土地,细查莫高窟中的每笔彩绘、鸣沙山上的每粒砂石,它仍愿意向你讲述千年历史中的点点滴滴,仿佛一切仅仅是瞬目之前。
免责声明:本站所有信息均搜集自互联网,并不代表本站观点,本站不对其真实合法性负责。如有信息侵犯了您的权益,请告知,本站将立刻处理。联系QQ:16407311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