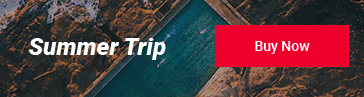历史文化街区60历史文化是哪几方面传播历史文化的意义
信息来源:互联网 发布时间:2023-10-25

他永远不会贸然地承认,尤其对他自己,离开这个城市的愿望其实是相互的——城市也想让他滚蛋。心甘情愿地离开与被赶出去可不一样,那无异于在平庸的对手面前俯首称臣,或者会被看成仓皇逃窜,那简直更糟糕。背弃故土多大程度上不是故土本身的离弃?不做孬种,是否还有可能逃开?无论答案是什么,这些疑问本身就是失败,他没有做好承担的准备。
抛弃者对于被抛弃者要保持优越感,要拥有爱人辞别一刻的清醒,从时间之线那辉煌耀眼而又无可阻挡的一点开始,他决定一个人生活。在开始个人离散之前传播历史文化的意义,如何保持住这种状态,是一个绕不过去的问题。他,移民之子,家中早有成例在先:他怕同事忘了他,怕出版社忘了他,怕以前的女人忘了他,怕追随他崇拜他的人忘了他,尽管并不认识他(正因为此,才会崇拜他),怕酒吧里的闲谈忘了他——离开者具有时效,名字会渐渐不被记起,直至再也不提。除了离开之外,他还需要让人怀念。这正是他的家庭20世纪70年代逃离祖国那场灾难时不曾做到的。
三十七年里积攒的社会资产尽管菲薄却又让人留恋,这与他的鄙薄形成了鲜明的反差:他不仅鄙薄自己的功业,而且鄙视这个建功立业的舞台——里约热内卢。他经常这样说里约,总在酒吧里收获反感:里约这个城市,倘若没有布宜诺斯艾利斯,会是远西的文化之都;倘若没有圣保罗,会是远西的金钱之都。在奥运会之前,它往前狂奔,要变成一个南半球犄角旮旯中的巴塞罗那,虽说穷了点儿,却更有风情,也更昂贵:房产的火爆加入到这不可逆转的进程中,止戈为武的新时代里,贫民窟养成了一种副热带米克诺斯的气派,里约南区小山上的陋屋变成了法国人发号施令的精品客栈。
倘若在20世纪初,尚且可以把那些狭窄的街巷、城中的睡棚、天花的源头与穷困的人统统拆迁掉,用来开辟奥斯曼式的大道,两侧修建新艺术风格的宅邸(后来,军事年代的经济奇迹中,这些建筑也被推倒,代之以毫无风格的摩天大楼),那么,在21世纪初,夷平这些山麓上的陋屋无论在上还是美学上皆不可行——尽管那里的条件与一百年前没有什么差别:垃圾堆积如山、暴力横行、下水道损毁、肺结核流行、城市病严重。1902年,当佩雷拉·帕索斯市长实行城市重建时,那些被逐出城市中心的男男正是毁山损林、把山丘变成贫民窟的人,这并非一种偶然。这是恶性循环,不是咬尾蛇,而是绕着自己的尾巴团团转的狗——在里约热内卢,在任何一个时期,这种景象都随处可见。
在21世纪第一个十年,有一种办法比夷平贫民窟更谨慎,也更有效,那就是在这个地方驻军,建起三米高的围墙,逐渐抽取当地居民赖以生存的氧气。窒息进程首先要掩饰这个突然之举,先把这块地方圈起来,给它开辟道路,之后将沿山麓而下的斜径与小路延伸出去,以迎接这些新人的到来:巴西武装部队的军官及其组织、承包商、房产中介、外国人、新资本家、银行、印刷厂、小馆子、抽象艺术画廊,American Apparel ,日式霜冻优格店占了老鞋匠的地盘儿,学设计的学生还被父母供养着却一个人占了原来六口之家的地儿,那里现在是一座豪华Loft、一座Upscale Condo、一个能看到海景的美丽小屋,只有25平方米,却要35万美元。这就是里约版本的中产阶级化,富有的社会阶层霸占了下等城区,原有的居民远离,哈克尼、格林尼治村、威廉斯堡、克罗伊茨贝尔、圣马丁运河、维迪加尔、坎塔加洛、罗西纳、帕汪-帕汪吉诺、曼格拉、普罗文登西亚、萨乌德,全都无可幸免。
“就像艺术一样。很难去精确地解释,但当你看到时,你就明白了。”一次,托马斯·安塞尔莫指着罗西纳的第一座星巴克,说了这番线年夏天开业。
最开始,咖啡的价格上涨了三倍,接下来房租飙升,之后,开始了买卖房产。这个里约南区的贫民窟历史文化是哪几方面,如今却被保护起来,任凭中产阶级侵略。有了正式的水电账单,正式的有线电视账单,正式的税收,正式的歹徒,甚至还有一个促进发展的文化项目,托马斯因此没日没夜地工作,研究音乐、Funk舞蹈、裹在少女上的小内内以及发情与约炮是如何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在这个原本的贫民区里高端大气起来的。
噪音一点儿没少。尽管新的殖民者——那些白人、老外(哪怕就是巴西人)——表面上对贫民窟的异类与喧哗都保持了容忍,但他们内心深处依然渴望清洁整饬。另一方面,原住民已经无法掩饰对这群沥青路移民者的轻蔑,也无法克制对耀武扬威的的愤怒——他们依然处于全副武装者的控制之下,对黑人与穷人,这些人说一不二。这么多年里,在这个地方,他们苦苦挣扎,于毒贩与或对立帮派的交火中苟活下来,如今却失去了栖身之所,赶走他们的人却没有做过哪怕一分钟诚实的工作。他们最终卖掉房子,投奔黑暗的郊区,却从未问过这个问题:“为什么当生活好起来时,我们却不得不离开?”
流浪汉、啃老族、混吃等死的人,不男不女的人,小角色、小明星、公知历史文化是哪几方面、骗人的计划,吐一口浓痰:妈!伊巴内玛这位活了四百年的女士,当她看到周日的阿波亚多尔被贫民窟的人占领,南海滩上躺满了欧洲的垃圾游客,大腹便便的酒鬼从分期付款的游轮下到基韦斯特,格林尼治村住满了康涅狄格乡下人,圣日耳曼大道的咖啡店塞满了无知的美国佬,乡村俱乐部的游泳池中充斥着蒂如卡的新富人,会生出同一种歧视,从21世纪第一个十年的后半段开始,在任何一个贫民窟,都会毫无羞耻地遭遇这种基于种族、社会等级与文化的阶级歧视。
几十年来,记者、桑巴舞者与社会学家用“社区”这个美词称呼贫民窟,如今,它已变成文化遗产的近义词,需要保护、展示历史文化街区60,需要国家资助与高墙。但这一切却总是为时已晚:贫民窟依然深陷战争之中。贫民窟于自身之中思念着波萨诺瓦黄金时期的里约热内卢。一些人甚至怀念军事时期——直到那时,这种对过去的相思,尚且是一种专利,只属于安居在沥青马路上铺着地毯的公寓里的退休人士。
里约北区与郊区非但鲜见于媒体,而且与“输出”的里约想象毫不相干,和南区相比,这里毫无风险,驱逐原住民的行动进行得更快、更无需遮遮掩掩。“改造”是个好借口,奥运会之前,这个词可以为所有暴行、强拆与强制移居辩护,无数人被赶出家园,把无限的土地让给说一不二的新主人:承包商及其政坛和军队里的同伙。门上的标记是一种宣判,四十八小时之内将拆除所有的房子,在奥托杜鲁姆、扎卡雷帕瓜、塔夸拉、康皮钮、玛杜雷拉、玛拉卡纳、奥拉利亚和港口地区,这一幕屡屡上演。
居民的重新安置权得不到尊重,批评改造行动的司法检察官横遭贬职,为了叫醒乞讨者,居然用上了泰瑟枪,政府公然发动“秩序威慑”行动,市政保安局未雨绸缪地赶走了流浪汉、游商和零工:这是时代的印痕,里约人选择了无视,承诺腐蚀了他们:一届世界杯,一届奥运会,四个地铁站、高速公路,博物馆、体育场——这是变成热带纽约的一厢情愿,是用一场城市整容就追上世界潮流的痴心妄想,它迟迟不至,却被报纸连篇渲染。
第一个十年里的最初几年,对于某些原住民而言,城市不再属于他们。住不起新里约的人被清理到黑暗溽热的郊区,在奥林匹克区域之外的地区,废弃的铁路两旁,居住点如病毒一般扩散。从海边到蒂茹卡的环形地带,不动产的价格由国际市场决定,与本地居民的真实购买力完全不能匹配:2013年,科帕卡巴纳海滩混凝土长路上一幢人满为患的公寓里,30平方米的开间租金与巴黎或纽约相等,是柏林或里斯本的两倍。
21世纪10到20年代的最初三年里,房产上涨了两倍或四倍,雷亚尔成了世界上最被高估的货币。这段时间,托马斯·安塞尔莫的财政顾问给他打电线点钟,威士忌杯子里加了苏打水和冰块,他的指尖在上面绕着圈圈,只是为了说:“我打算把所有的钱包括我们买的那个股票基金挣的钱都投到货币基金上去,我和内部人士谈过了,市场是笔糊涂账,因此,所谓保本挣钱纯属胡说八道。”
人民毫不知情,各种年龄的巴西人咬紧牙关对付生活成本的上涨,他们自豪地再现纽约时报与卫报的黑字标题,却对下面这件事毫无质疑或故意忘却:过多的货币催生了风险借贷,支持着那些著名的们的事业,并危害着工业竞争性。当2009年,就在大天使加百列公布奥林匹克预言后不久,《经济学家》在11月刊出了一篇文章,说巴西在“2014年之后”的那个十年会成长为世界第五大经济体,超越英国和法国。巴西唯一的危险在于其过分的自豪感,因为和印度相比,巴西没有种族冲突和;和俄罗斯相比,巴西出口的不仅仅是武器和石油,未来之国已成过眼云烟,人们却相信它的未来业已到来。
“那期《经济学家》把腾飞的像作为封面,这成为了我们崩溃的起点。人们把这本杂志贴在全城的写字楼里,仿佛是一幅祭坛画。大多数人从未读过这篇讨论巴西魔幻般未来的20页的专题,但对此坚信不疑。现在的日子啊!还是过去好!”他们把那一套当成神谕,仿佛写这篇文章的人不是那群与别西卜的投资基金关联紧密的美国记者,而是一位迷狂中的使徒,他书写下上帝以号角一般的声音向他描绘的天堂并奉命将启示录送往亚细亚的七个教会。在那一刻,我们相信繁荣是命中注定——然而不幸的是,这并非我们最后的天真。还是任《经济学家》复制一个关于巴西的圣约翰启示录吧,因为此刻古老的一切消失殆尽,那么多人的眼中却流不出泪水,这一点毫无疑问。
迷茫时分,托马斯·安塞尔莫抱怨的不仅是圣塞巴斯蒂安海滩越来越贵的物价,而且,这一切距离他童年与少年的回忆越来越远。街上的电影院与书店不见了,他曾在此终结了梦游般的少年时光,取而代之的是福音教堂与健身馆。黄铜灯柱与橙黄光源的法式街灯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荧光灯太平间一样的照明,洒在路上,现出苍白的金属色——里约的新式灯光是一个谎言,只为掩盖这个城市永恒的黑暗。酒吧、饭店、不见了,它们古老的名字早就丧失了本义,比如:忠贞之罚、月亮吧、车库、皇家阿斯托里亚、69、基地、乔托、沙坑、同志70,等等,取而代之的是不断延长的玻璃怪兽,药店和化妆品店毫无理性地倍增,每个街区甚至有好几家。这些大厅中每一处空余空间中都塞满了洗发水架子与媚俗的装饰,托马斯隐隐看到一个水族箱,桌与椅的空荡回忆盛放其中,朝向一种让他自己害怕的遗忘,直至每一个阳台的最后一张照片终于在最后一个抽屉里焚毁。
死去的并非只有电影院和酒吧,另外一种旧时光的见证者也死去了:里约热内卢广场上的雕像或是消失,或是被贼偷走融成金属,尽管广场装上了围栏,防止乞讨者进去睡觉。在公共行道上,瓦伦汀大师的爱之泉天使,少了翅膀和胳膊。在十五广场,奥索里奥将军的佩剑与巴拉圭战争的大炮一起融成了铜。在科帕卡巴纳的石子路上,背海而坐的诗人特鲁蒙特的眼镜不见了——眼镜被偷了,这样他至少不用再看眼前的车流与楼群了,是命中注定,要他生生世世注视这副丑陋的风景。
一个男人囚禁了自己,他的双脚束缚在地面上,目光呆滞而迟缓:这雕像是他自己,四十岁前就已老去,仿佛每一日都是从一幕剧与另一幕剧之间的大醉中惊醒:我怎么来的这里?这个城市是哪儿?在这花团锦簇似曾相识的叙述之中,他迷失了方向,重建这条路仿佛不可能,因为这意味着将双脚从地上拔起,或终于踩踏在大地上。托马斯·安塞尔莫不知如何开始。
崩溃之前的几年里,托马斯·安塞尔莫没有站在路上清算自己的损失,而是把自己关在家里,打开空调,把香槟倾倒在马天尼杯中,与女人举行小型狂欢。镇静剂作用下传播历史文化的意义,他不发一言,也不去写作,只是用刚买的设备录下音乐:凌乱的低音、吉他的反复段落,无休无止的延迟效应,制造氛围的鼓点,世界末日的总括。之后,他用几个小时来缩混音乐,努力给自己而又哀伤的创作找一个合适的标签:寒潮、屏幕保真、超级扰动流行曲、极简电动自赏派传播历史文化的意义、失重迷幻氛围,等等。欢宴结束,在他睡觉之前,他会关闭电脑里的音乐,它们只为这位衣着清凉的挑剔听众而作——在他不写作也不工作的五年里,这就是他的观众与舞台。
如果他所剩不多的朋友(他们自称“抵抗力量”)邀请他晚上参加舞会,他会先臆想一番那些已经不存在的酒吧和,之后便开始老调重弹:“出门?我最希望的就是人们都回家。”或者传播历史文化的意义,“舞会最大的用处是让单身汉找到心仪的姑娘。其他人在那里是在污浊的空气里浪费时间。”托马斯觉得自己没有理由离开这座五十平方米的清凉宫殿离开这安静的家的荒漠去寻觅女人,再之后,他开始絮絮叨叨,亲近的朋友都会背了,他会说里约人的这种自我感觉良好真不可忍受,会说焕然一新灯火通明的拉帕如今成了游客的巢穴,这真够愚蠢的,也够黑暗的,会说当代巴西没有一个人能作出吸引他走出家门的音乐和戏剧,会说城中的诗人只会写无聊的绕口令而小说家只会复制死去的传统,他还会说和城里的艺术家坐在同一张桌子边让他觉得是在受刑:那些人思想浅薄,满脑成规,然而却对权贵、家长制、不合时宜的强势意见以及忽悠钱的关系网奴颜屈膝。
本世纪第一个十年,里约的一张桌子前,艺术家们浪费着世界的时间,彼此交换项目与计划信息,他们可以分成两大类:一种人额头上贴着标签——拿了政府的钱;而另一种人额头的标签则是——拿了电台或其赞助商的钱。不属于这两个圈子的人,会去争夺人家不要的残羹剩菜,他们殚精竭虑地四处活动,结交那些在结构复杂人浮于事的宣传机构中任职的要人,结识制片人,联系电台、报纸和电视台,时刻注意三个层级的国家政权的通告、奖金与资助。
托马斯·安塞尔莫可没有纯情到对这些活动一无所知,或者不知道如何攫取钱财、名声与女人。正相反,他对此了如指掌。问题是那个标签,那个贴在额头的标签,厚着脸皮贴上标签很容易,不会让他痛苦,问题是那种明明白白,是用耳光换取飞黄腾达,污秽与平庸都不是问题,问题在于太过廉价。
因此,为了居住在这个观念的坟墓里,人要付出巨大的代价,这里的气息仿佛公共浴室般污秽,去一次雷布隆的面包房,仿佛开始了好莱坞之旅,人就像狗仔队,在摩托车上搭设办公室,就在名人在展览上亲吻情人的一瞬,将照片恰到好处地发在网上,从酒吧餐台到市政剧院,这里的海滩,这里的任何一个地方,都是伸展台,里约人在这里实现看与被看的心愿;在这里所有人都是故乡的异乡人,区分成无可计数的社区、区域历史文化街区60、贫民窟、街区、小区、球迷协会、桑巴舞校、犯罪集团、街角、沙滩亭和酒吧餐台,对于托马斯和那个不断增长的沉默少数而言,这个城市已不再具有意义,他们不但搬离了街区,而且决绝地放弃了城市,不是因为缺钱,而是因为再也不堪忍受。托马斯·安塞尔莫就是以这样的方式相信着21世纪第一个十年,这个黄金年代。
尽管善于自欺,但托马斯知道这个长满了树装满了人正说着再见的国度与城市只是他自己,托马斯·安塞尔莫。他,从不曾放弃过任何东西,一向是其他的人与事放弃他——或是职务,或是女人——当他意识到自己从未放弃过时,他终于惊呆了
1978年出生于里约热内卢。多部作品曾入选巴西与国外作家合集。著有小说《此刻的身躯》[Corpo Presente,全球(Planeta)出版社,2003],《马斯楚安尼之日》[O dia Mastroianni,行动(Agir)出版社,2007],《爱情故事的唯一幸福结局是车祸》(O nico final feliz para uma hist ria de amor um acidente,文字出版社,2012),这本小说在葡萄牙、西班牙和德国也获出版。2007年,Hay Festival与波哥大世界图书节将他选为拉美39位39岁以下最出色小说家之一。
免责声明:本站所有信息均搜集自互联网,并不代表本站观点,本站不对其真实合法性负责。如有信息侵犯了您的权益,请告知,本站将立刻处理。联系QQ:16407311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