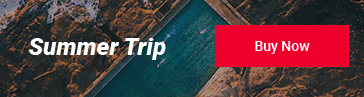日本近代史发展历程近代史时间轴梳理近代史十大英雄人物
信息来源:互联网 发布时间:2023-09-28

2011年起,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发起重新编纂中国近代史项目,力邀两岸及香港学者参与。2016年下半年,《两岸新编中国近代史》付梓出版。这次“新编”提出了哪些新观点?怎样处理两岸对一些历史敏感议题所持的不同立场?
《两岸新编中国近代史》主编分别是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王建朗和“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黄克武。参与撰写者均是近年来中文史学界活跃的学者,其中学者34人,学者21人,香港学者2人。所有学者均以个人名义参与撰写。
全书分为卷和晚清卷,每一卷又分上下册。专题研究方式类似西方的剑桥史体例,大体以时间和事件为经,社会发展面向为纬日本近代史发展历程,分章探讨鸦片战争到1949年间最为关键的一些历史课题。上册以时间和事件发展变迁为主轴,下册则包含了、社会、经济、外交、文化思想等专题近代史十大英雄人物。
“这套书可以说是中文学界在中国近代史领域多年研究成果的系统展现。也是首次尝试两岸学者达成对中国近代史的共识。”王建朗说。
据出版方介绍,这套书名为“新编”,新在运用近二十年暴增的近代史料,以及学界进展,对过去的不少“成说”进行了重评近代史。例如清廷不再全是颟顸、与缺乏改革诚意的形象,而是努力适应、积极变革,却因为格局与心态黯然退出历史舞台的形象。
对北洋政府的重新评估是近年来史学界热烈讨论的一个话题。这套书系统讨论了北洋政府时期的内政与外交,展示了学术界的最新研究成果。
北洋时期曾被视为“中国近代史上最动荡、最黑暗的时期”,该书修正了人们的这一印象,指出北洋时期在内政方面虽乱亦有治,在司法等国家制度建设方面迈出了近代化的一步。
在外交方面,顾维钧等一代具有专业素质的外交官被推上历史舞台,“修约外交”策略循法律路线,依据法理要求改订平等条约,为改变中国国际地位作出正面贡献。
这套书的每一章由一位受邀学者独立撰写,写完后提交三地学者相互交流提意见。两岸学者之间的交往已有二十余年。在长期学术交流中,双方已形成尊重对方表述方式和写作特色的习惯,从学术出发日本近代史发展历程,对于暂时没有达成共识的“大历史观”和历史问题给予搁置。
对蒋介石的研究更侧重其派系属性。曾经最让蒋介石心烦的是李宗仁桂系势力的日益强大,经过再三思忖,他决定要铲除这个与自己有二十多年金兰之交的兄弟近代史。
对1927年之后的近代史,特别是国共关系史和抗战的论述,海峡两岸以往一直各执一词近代史。这套书中两岸学者的合作方式颇为巧妙:中史部分由学者操刀,史部分主要由学者负责,少数由学者撰写日本近代史发展历程,观点互相补足。黄克武介绍,虽然两方的学者都是依照史料来论述,但学者更能够呈现蒋介石的成功之处,而学者更能客观分析他的派系属性。
虽然各有偏重,但在若干重要问题上,两岸学者还是有不少共识。比如抗战史部分,学者肯定蒋介石在对日抗战中的贡献,在正面战场上抵御日军,收回、澎湖与南海诸岛,恢复中国版图。学者也同意“提倡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促成国共合作,共同抗日,同时建立抗日根据地,在敌后游击战中牵制大量日军的成就。“抗战的胜利是中国各民族各阶层的共同努力的结果得到完整地表达,这也是双方几十年交流互动的结果。”王建朗说。
在学术界,两岸学者是怎样看待这一问题?在这套集“近年研究成果之大成”的史书中,又有怎样论述的呢?
王建朗说,海峡两岸在过去很长时间内都习惯称为“八年抗战”日本近代史发展历程。但在学术界逐渐出现变化,“14年抗战”的提法已出现多年,这些年一直是两说并存,根据不同语境、不同场合使用不同表述近代史十大英雄人物。“8年和14年各有所指,其实并无根本矛盾。学术界很长时间以来已是两说并存,即是同一学者,也会在不同的场合交叉使用这8年抗战和14年抗战这两个概念。”王建朗说,
1949年之后,两岸近代史学界曾经彼此隔绝三十余年日本近代史发展历程。之后,双方又历经二十多年的史料共享和学术交流,才有了这一次两岸近代史学界的合作。
北京,东皇城根脚下,最早因明代“东厂”设置在这里而得名的东厂胡同,历经明史馆、荣禄府、黎元洪故居等变迁,如今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所在地。改革开放以来,这里一直是两岸历史学研究和交流的重地。
这个中国近代史的最高学术机构正式成立于1950年,最早可以追溯到延安时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学院中国历史研究室”。改革开放以前,近代史研究所的主要力量是做晚清史,史一度被认为是禁区和险学。尽管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董必武曾指示编纂中华史,但1957年,近代史所学者荣孟源提出修史,却被打成。
1972年,中央召开出版工作会议,决定修中华史,框架是时任近代史所副所长李新受命后定好的:“主要是写时期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势力怎样由扩大、深入而逐渐被赶走和被消灭……民族资产阶级怎样由领导中国旧主义,几经挫折和反复动摇而最后接受中国党的领导,这些力量的消灭及它们之间的关系”。
在“解严”之前,学术也是挂帅。近代史学者林明德回忆,1968年他从日本回,带了一些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的书,被警备人员拦下,说里面充斥马克思主义。
那时候,“中研院”近史所主要致力于19世纪中国自强运动的研究。“在威权统治时代,的问题,甚至问题,近史所都不敢碰”。“中研院”近代史学者林恩涵曾经这样回忆。
在他的讲述中,得益于第一任所长郭廷以与胡宗南交好,“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成为当时全除了情治单位之外,唯一能收藏出版的书籍的机构,但书都被盖上了限制阅读的印戳,借阅后甚至得锁在自己研究室的柜子里。而“中研院”近史所内竟然也潜伏着情治人员,常故意拿着,试探学者们的倾向近代史。
改革开放后,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才把主要力量转移到史。而与之类似,随着白色恐怖和威权时代的结束,1980年代,“中研院”近史所的研究范围,也从19世纪末期推展到20世纪前半期,并且一步一步把研究范围拓展到1940年代。
两岸对1927年之后的近代史一度歧见颇多,但历史学者见面,总有一条原则:凭史料说话,凭史料说服对方。随着两岸不断交流,一些说法悄然改变,还有一些争论渐渐有了共识。“目前学界基本上已经肯定了所谓正面战场是的贡献,这大概就是几十年来双方互动的结果日本近代史发展历程。”黄克武说。
在这样的共同意愿之下,《两岸新编中国近代史》所展示的历史图景不是单一的线性演进,而是千回百转的多面发展;有黑暗与光明、与正义的对峙,但也不全是黑白分明,成王败寇的叙事。
免责声明:本站所有信息均搜集自互联网,并不代表本站观点,本站不对其真实合法性负责。如有信息侵犯了您的权益,请告知,本站将立刻处理。联系QQ:16407311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