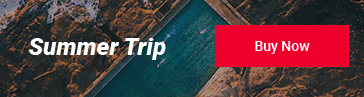近代史有哪些书籍与近代史相关的书籍
信息来源:互联网 发布时间:2023-09-22

民國初年,以《新青年》和北京大學為核心,許多頗有才華的作家漸次聚攏在北京,他們共同開啟了歷史的新紀元。“五四”一代的帶路人無疑當推陳獨秀,魯迅曾回憶說:“《新青年》的編輯者,卻一回一回的來催,催幾回,我就做一篇,這裡我必念陳獨秀先生,他是催促我做小說最有力的一個。”從1916年11月到1920年初,陳獨秀在北京生活了不過三年多一點,時間並不算長,但是在這段時間裡,他被聘為北大文科學長,直接組織領導了震古爍今的“新文化運動”,間接影響帶動了“五四運動”,促進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因此從陳獨秀一生的思想軌跡來看,在北京的這段經歷可謂具有承前啟后的重要意義。
前門西河沿街位於北京正陽門以西,現在這裡還保留著不少民國乃至滿清時的建筑。胡同西口的正乙祠是清朝康熙年間浙江商人修建的銀號會館戲樓,歷經三百余年,現在是中國最老的、且保存基本完好的純木結構戲樓﹔胡同中段路北一座二層小樓,門楣上“察哈爾興業銀行”的字跡清晰可見﹔不遠處一座形制相仿的二層小樓,中間的宅門明顯是被封上的,門楣上的字已然不甚清晰与近代史相关的书籍,旁邊的標牌上提示這裡曾是一家眼藥店。盡管離前門、大柵欄近在咫尺,但恐怕沒有多少人知道這裡曾經是聚集了金融業、旅店業、餐飲業的繁華熱鬧所在,想必更沒有多少人知道大名鼎鼎的陳獨秀初到北京就住在這條北京最早的“金融街”上。
1916年11月28日,37歲的陳獨秀住進了北京前門外西河沿的中西旅館,同行的還有上海亞東圖書館的創辦人汪孟鄒。這是陳獨秀第一次北上進京,之前他一直在日本、上海、安徽等地辦報,此次進京也本是為了將亞東圖書館、益群書社合並改為“大書店”。但是蔡元培的造訪顯然改變了陳獨秀的原定計劃。西河沿的南邊便是書肆雲集的琉璃廠,陳獨秀自然免不了要去“打卡”。巧的是,在琉璃廠陳獨秀碰到時任北大教授的老友沈尹默,沈尹默又把這次巧遇講給陳獨秀在日本留學時的故交、時任北京醫專校長的湯爾和。沈、湯都是蔡元培信任而且倚重的朋友,他們都向蔡元培舉薦由陳獨秀出任北大文科學長。蔡元培對於陳獨秀和他辦的《安徽俗話報》“本來有一種不忘的印象”,再加上湯爾和還拿著幾冊《新青年》告訴蔡元培“陳君現改名獨秀,主編《新青年》雜志,確可為青年的指導者”,這越發堅定了蔡元培“決意聘他”“與之訂定”的決心。
當年12月26日与近代史相关的书籍,蔡元培正式出任北大校長,就在當天早上9點,蔡元培專程到中西旅館來拜會陳獨秀,力邀陳獨秀擔任北大文科學長,“道貌溫言,令人起敬”。可陳獨秀卻以正在辦雜志為由回絕了,蔡元培則表示可以把雜志一起帶到學校裡來辦。據同行的汪孟鄒記述,“蔡先生差不多天天來看仲甫,有時來得很早,我們還沒有起來。他招呼茶房,不要叫醒,隻要拿凳子給他坐在房門口等候。”經過幾次這樣“三顧茅廬”式的邀請,陳獨秀最終應允下來。由辦報到辦學,從游蕩皖滬到定居北京,西河沿胡同裡同蔡元培的幾番會面直接改變了陳獨秀的人生軌跡,這對陳獨秀來說是有轉折意義的。
受到維新思想的影響,陳獨秀“弱冠以來,反抗帝清”,武昌起義期間一度參政,護國運動當中堅持“倒袁”,先后署理《國民日日報》《安徽俗話報》《甲寅》以及《青年雜志》。多年從事的挫折使陳獨秀深感中國陷入“生機斷絕”的境地,而之所以遲遲無法擺脫亡國的危機,主要在於中國人“漠視國事”“殊令人心寒”。在“五四”一代知識分子中,陳獨秀可能是最早開始反思“國民性”問題的。在長期的斗爭實踐中,陳獨秀深刻意識到要想改變國家的命運,必先開啟民智、爭取民權、改變民性,必須從思想文化層面徹底地重塑一個“想象的共同體”,在他看來,這才是最為長遠的問題,是“最后覺悟之最后覺悟”,這也是他日后與《新青年》同人一拍即合的關鍵,是他貫穿於辦報、辦學過程的思想線索。
1917年1月13日,北洋政府教育部專函回復了蔡元培以北大校長的身份提出的請求,批准陳獨秀擔任北京大學文科學長,1月15日陳獨秀走馬上任。哲學系學生馮友蘭曾回憶說:“他(指蔡元培)到校后,沒有開會發表演說,也沒有發表什麼文告,宣傳他的辦學宗旨和方針。隻發了一個布告,任命陳獨秀為文科學長。就這幾個字,學生們全明白了,什麼話也用不著說了。”陳獨秀到任之后,“文科的教授也多了,學生也多了,社會對於文科也另眼看待。學校是變相的科舉的觀念打破了。學生中間,開始覺得入大學的目的是研究學問,並不是為得個人仕途的‘出身’”。
不久陳獨秀將家眷和《新青年》編輯部全都安頓在東城的箭杆胡同裡,1917年2月1日發表《文學論》時,陳獨秀已經住進這個小院了。箭杆胡同往北不遠便是北大,當年這一帶是北大三院學生宿舍。胡同其實有些偏僻,不知從何時起,胡同東段已經堵死,成了個死胡同,整條街上隻留下了陳獨秀曾經住過的院子。院子原本分東西兩個部分,西院為房東居住,東院租給陳獨秀,陳獨秀和高君曼以及陳鶴年、陳子美住在南房,將北房留給《新青年》做編輯部。在建黨百年之際,經過騰退、修葺,箭杆胡同的這處陳獨秀故居已面向公眾開放,去年伴隨著電視劇《覺醒年代》的熱播,一時間游人如織。
陳獨秀最初計劃試干三個月,但實際做了有兩年半,在北京期間,他的大部分時光都是在這個偏僻胡同的小院裡度過的。陳獨秀的生活並不算寬裕,但與李大釗、胡適在北京時的多次遷居不同,陳獨秀很快就租下了箭杆胡同的這套院子,直到他后來黯然離京,其間一直沒有搬過家。這似乎也說明陳獨秀在北大備受尊崇和優待。從薪酬薄上可知,陳獨秀300元的月薪雖然略低於理科學長夏元瑮的350元,但名字排序卻僅在校長蔡元培之后,位居第二,並且300元的薪酬也僅次於蔡、夏,在全校排第三。1918年10月,北大紅樓建成,陳獨秀的文科學長辦公室在二層樓梯口左手邊南側第一間,非常寬敞,光照甚好。
隨著陳獨秀和《新青年》的到來,從1917年4月起,周作人、李大釗、胡適、錢玄同、劉半農以及魯迅等先后在北大執教,不難想象,新文化運動的同人們會頻繁出入於箭杆胡同,小小的庭院在歷史上卻曾是鴻儒聚首的地方。《新青年》使得北大成為新文化運動的核心,假如沒有《新青年》及其廣泛傳播,新文化運動在北大校園之外也引起廣泛的社會影響,這恐怕是難以想象的。也正因此,新文化運動可以說正是由北大和《新青年》,尤其是箭杆胡同時期的《新青年》這“一校一刊”雙輪驅動的。而為這雙輪掌舵的當然是陳獨秀。胡適曾說文學的進行,最重要的急先鋒是他的朋友陳獨秀,“陳獨秀的特別性質是他一往直前的定力”。魯迅雖戲稱自己當時的創作是“遵命文學”,“既然是吶喊,則當然須聽將令的了”,但卻又很嚴肅地講道:“不過我所尊奉的,是那時的前驅者的命令,也是我自己所願意尊奉的命令”,“那時的主將是不主張消極的”。
在許多人的印象中,陳獨秀脾氣火爆、性格執拗,頗有“家長制”的作風,這並非毫無來由。英文系學生許德珩和陳獨秀之間曾有一樁趣事:陳獨秀整頓課堂紀律,他“不調查研究,誤聽人言”,把黎元洪侄子的缺勤記在許德珩頭上,許德珩“十分驚異,並極端憤怒”,砸碎了布告牌。陳獨秀大怒,因之又記過一次。許德珩再次砸了布告牌,並且站在陳獨秀辦公室門前搦戰,要同他說理。此事立刻為蔡元培所知悉,經蔡調查,搞明白了原來確實是陳獨秀弄錯了,責令陳收回成命,好言勸慰。陳獨秀為人剛勁、猛毅,同文質彬彬的蔡元培、胡適等絕不相類,但也正是這種性情使得他無論蒙受什麼樣的挫折和打擊,仍時時蓄存著相當的決心和信心,以“必不容反對者有討論之余地”的堅決和凌厲同各種守舊勢力展開毫不妥協的斗爭,包括在日后抓住歷史機遇創建了中國共產黨。值得一提的是,陳獨秀和許德珩后來冰釋前嫌,1919年冬陳獨秀出獄之后,許德珩還受李大釗之托幫陳獨秀在上海尋找房子。后來,陳獨秀客居江津,許德珩還多次去探望,從中也不難看出許德珩對陳獨秀的敬佩。事實上,陳獨秀為人處世上雖然有強勢的一面,但也頗有海納百川的一面,新文學同人其實並非那樣親密無間,尤其胡適同其他幾位的關系都很一般,假如沒有陳獨秀的領導、維系,很難想象北京時期的《新青年》能大獲成功,產生空前的影響。
1918年1月,《新青年》正式改為同人刊物,由李大釗、錢玄同、高一涵、沈尹默、陳獨秀、胡適等六人輪流主編,“所有撰譯,悉由編輯部同人,共同擔任”。有研究稱,《新青年》在創刊之初發行量大約在一千份左右,1917年之后“銷數漸增,最高額達一萬五六千份”。《新青年》的讀者數量可能比這個銷售額還要多,比如像先前湯爾和拿著幾冊《新青年》給蔡元培看,類似這樣一份刊物幾人傳閱的情況,在清貧的學生群體當中恐怕要更多,因而到底有多少人受到陳獨秀和《新青年》的影響、鼓舞,實在難以確數。毛澤東后來曾講:“《新青年》是有名的新文化運動的雜志,由陳獨秀主編。我在師范學校學習的時候,就開始讀這個雜志了。”從訓蒙樹人的目的出發近代史有哪些书籍,陳獨秀特別看重音樂、體操等美育的方式與內容,認為傳統教育重德育、輕智育和體育,“都把音樂、體操,當作無關緊要的學問”,“以至全國人斯文委弱,奄奄無生氣,這也是國促弱種的一個原因”。陳獨秀的這種看法似乎也引起了青年毛澤東的興趣,他以“二十八畫生”為名,將自己寫的《體育之研究》寄到箭杆胡同,陳獨秀將其發表在1917年4月出版的第三卷第二號《新青年》上。
在北大校內,陳獨秀推行了一系列課程、制度改革,大力支持文科師生成立各種研究社團﹔在校外,他以《新青年》為思想文化陣地,旗幟鮮明地指出“舊文學、舊、舊倫理,本是一家眷屬,固不得去此而取彼”,“要擁護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孔教,禮法,貞節,舊倫理,舊﹔要擁護那賽先生,便不得不反對國粹和舊文學。”以“科學”“”為核心的進步思想得以迅速傳播,中國社會掀起了一股思想解放的潮流与近代史相关的书籍。雖然陳獨秀“打定二十年不談的決心近代史有哪些书籍,要想在思想文藝上替中國建筑一個革新的基礎”,但事實上,在他的影響之下,一大批才識卓著的青年人前仆后繼地投身到救亡圖存的隊伍中來。
除去西河沿、北大紅樓和箭杆胡同,北京城裡還有幾處也和陳獨秀密切相關,而且還見証了陳獨秀的思想轉型。其中一處便是城南菜市口附近的米市胡同。1918年,為了出版《每周評論》,想必陳獨秀也曾多次出入這裡吧。
陳獨秀很早就關注社會斗爭,而且還直接參與過拒俄、反清、倒袁的活動,這和許多知識分子的經歷大不相同,作為一個經歷和經驗都非常豐富的宣傳家,在民國初年“城頭變幻大王旗”的氛圍裡,陳獨秀是不可能完全回避的。在箭杆胡同裡編輯《新青年》時,他就發表過不少指點江山的文字。1918年11月,伴隨著歐戰結束,國內一時陷入“公理戰勝強權”的狂歡之中,蔡元培、李大釗等紛紛發表演講、撰寫文章,他們都屬意那些被壓迫的勞工、庶民。特別是李大釗,展望著“庶民的勝利”“Bolshevism的勝利”(即“布爾什維主義的勝利”),朝著馬克思主義的思想轉型已經非常明顯。國內洶涌的愛國熱情使得陳獨秀認為“不談”的“戒條”已經落后於形勢的發展,從而決心再創辦一份比《新青年》“更迅速,刊期短,與現實更直接”的刊物,介入“主張公理,反對強權”的討論中來。
11月27日下午,陳獨秀在他的辦公室裡召集了李大釗、周作人等人,議定編輯出版《每周評論》,12月22日《每周評論》創刊,每周日出版,8開4頁,一直持續到第二年8月30日被北洋政府封禁,共出37期。刊物發行所就在米市胡同79號院、原來的安徽涇縣會館裡。米市胡同形成於明朝永樂年間,迄今已經有六百余年歷史了。滿清時期,米市胡同所處的宣南一帶修建了大量的會館,康有為曾住過的南海會館也在這條胡同裡。令人遺憾的是,進入新世紀后不久,米市胡同就消失在城市改造的轟鳴與等待之中,涇縣會館早已被夷為平地,康有為故居也前途未卜。
《每周評論》的創辦顯然是陳獨秀思想轉折的重要體現。在編輯《每周評論》期間,陳獨秀以“隻眼”為筆名就裁兵、禁煙、廢督、組織國會、南北議和等國內的問題頻頻發表意見,而且在他的指揮下,《每周評論》從一開始就特別關注山東問題與巴黎和會,而這恰恰是時局的熱點、焦點所在,《每周評論》也因此迅速產生了巨大的影響——“這時代,各地的學生團體裡忽然發生了無數小報紙,形式略仿《每周評論》,內容全用白話。此外又出了許多白話的新雜志。有人估計,這一年(一九一九)之中,至少出了四百種白話報”,其中即包括孫中山委派專人創辦的《星期評論》《建設》以及毛澤東創辦的《湘江評論》。
1919年4月底,北洋政府在巴黎和會上遭到徹底失敗,“公理戰勝強權”的迷夢完全破滅,受《新青年》《每周評論》影響的青年學生在激憤之中聚集起來,在蔡元培、陳獨秀的組織、策動下,“五四運動”隨即爆發!在“五四”當天出版的《每周評論》上,陳獨秀憤然戳穿道:“巴黎的和會,各國都重在本國的權利,什麼公理近代史有哪些书籍,什麼永久和平近代史有哪些书籍,什麼威爾遜總統十四條宣言,都成了一文不值的空話。”在隨后的幾期中,他不斷發表文章抨擊北洋政府的賣國行徑,召喚國民的愛國之心,鏗鏘有力地提出“強力擁護公理。平民征服政府”。
短短兩年的時間,得益於《新青年》《每周評論》的廣泛傳播和進步思想的深入影響,陳獨秀成為一時的焦點人物,從之前的精神領袖、文化偶像開始朝著領袖、社會精英轉型。不同營壘對他的評價也開始兩極分化。擁戴者稱贊他是“思想界明星”“五四運動時期的總司令”近代史有哪些书籍,敵視者則極盡詆毀、中傷之能事。比如1919年2月17日,主張維新、忠君保皇的林紓發表《荊生》,以田其美、金心異、狄莫分別影射陳獨秀、錢玄同和胡適,說他們三個人在陶然亭發表反孔言論,遇到“偉丈夫”荊生,對三人嚴加訓斥、大打出手,田其美等屁滾尿流,落荒而逃﹔稍后又作《妖夢》,以田恆、元緒、秦二世暗指陳獨秀、蔡元培和胡適,其中田恆“二目如貓頭鷹,長喙如狗”,他們游歷陰曹地府,最終被阿修羅王抓住吃掉,“積糞如丘,臭不可近”。在茅盾創作於20世紀40年代的小說《霜葉紅似二月花》裡,霸佔善堂的趙守義把“陳獨秀”喚作“陳毒蠍”,這些都反映了文化保守勢力對陳獨秀的敵視。
1919年3月26日晚上,迫於壓力,蔡元培與“關系諸君”在湯爾和家中會商,討論陳獨秀在北大的去留問題,“十二時客始散”。會上,湯爾和、沈尹默的發言都極不利於陳獨秀,這恐怕是最讓人費解與唏噓之處,因為當初正是他們二位向蔡元培舉薦陳獨秀。不久陳獨秀便被變相免去了文科學長的職務,可謂陷入空前孤立的境地,腹背受敵。“五四”之后,因為學生抗議聲浪巨大,整個形勢急轉直下,陳獨秀明知“在京必多危險”,但仍堅持抗爭,6月11日午后,在北京“新世界”游樂場散發指導“六三”運動的《北京市民宣言》時被捕。當晚,箭杆胡同陳宅亦遭查抄。
“新世界”游樂場大致位於現在北京萬明路、香廠路十字路口的東北角。民國初年,朱啟鈐在這一帶仿照上海的“大世界”打造北京的“新市區”,繁華熱鬧一時無兩,后世有人認為具有“把北京從封建都市改建為一個現代化城市”的意義,位於十字路口東北角的“新世界”游樂場和西北角的東方飯店便是這個宏大工程的產物。想必也正是因為游人如織,所以陳獨秀才選擇在這裡散發傳單的吧。現在,萬明路、香廠路的十字路口與尋常巷陌無異,隻不過東方飯店還屹立在原址,並且還加蓋了新的大樓,而“新世界”則顯得命運多舛,如今佔據原址的是一幢普普通通的高層塔樓与近代史相关的书籍,讓人無可憑吊。
陳獨秀案震動一時,社會各界紛紛聲援,李大釗痛斥曰:“現在好久不見‘隻眼’了。是誰奪走了我們的光明?”迫於壓力,三個月后北洋政府釋放了陳獨秀。轉過年來陳獨秀曾短暫南下,返京后由李大釗護送於1920年2月離京避難,隨后在上海創建了中國共產黨。
“南陳北李,相約建黨”是中國共產黨創建初期一段常常被人傳頌的佳話。陳獨秀對歐洲尤其是法國思想文化一直抱有濃厚的興趣,所以很早就了解到社會主義學說。隨著局勢的發展和《每周評論》的創刊,陳獨秀的思想已經發生很大轉變,例如他曾講:“歐洲各國社會主義的學說,已經大大地流行了。俄、德和匈牙利,並且成了共產黨的世界。這種風氣,恐怕馬上就要來到東方。”當然,相比同期李大釗在《我的馬克思主義觀》等文章中對馬克思主義專門、深入的介紹、討論,陳獨秀很明顯是滯后於李大釗的,至少不像李大釗那樣已經從個人意識中的關注、傾心轉換為有目的的研究、宣傳。1919年6月8日,陳獨秀發表了包括著名的《研究室與監獄》在內的一組“隨感錄”,提醒大家“立憲和政黨,馬上都要成歷史上過去的名詞了,我們從此不要迷信他罷。什麼是?大家吃飯要緊。”三天后,陳獨秀被從研究室抓到了監獄中,經過三個多月的思考,出獄之后陳獨秀明確提出要“和過去及現狀各派政黨,絕對斷絕關系”,這或許可以視為已經具備了建立新型政黨的思想沖動﹔緊接著他還指出“絕對沒有財產全靠勞力吃飯的人”,那些“沒有財產的”被剝削、被壓迫者要“合成一個無產的勞動階級”。由此可見,在離京之前,陳獨秀與馬克思主義已經相當靠近了。
離開北京之后,陳獨秀在上海重組《新青年》編輯部,1920年8月陳獨秀在上海建立了中國共產黨的第一個早期組織,9月《新青年》第8卷第1號改版為黨的早期組織的機關刊物,公開宣傳馬克思主義,為黨的創建做了思想上近代史有哪些书籍、理論上、上的准備。歷史的新局由此漸漸展開与近代史相关的书籍。
黨的早期組織最先是在上海成立的,但思想的火種卻是從北京點燃、傳遞過去的。陳獨秀在北京的三年多時間裡說不上春風得意,北京時期的陳獨秀總給人一種“未完成”感,“新文化運動”仍然時時遭到保守勢力的反扑,“五四”所開啟的民族自強、復興之路尚前路漫漫,所以回想起這一時期的陳獨秀總讓人有一種壯志未酬的遺憾,這似乎正應了他早年寫的一句詩:“男子立身惟一劍,不知事敗與功成。”在陳獨秀去世80周年之際,踏著陳獨秀在北京的足跡,敬佩、惋惜、欣慰似乎都兼而有之,可謂五味雜陳吧。
人民日報社概況關於人民網報社招聘招聘英才廣告服務合作加盟供稿服務數據服務網站聲明網站律師信息保護聯系我們
免责声明:本站所有信息均搜集自互联网,并不代表本站观点,本站不对其真实合法性负责。如有信息侵犯了您的权益,请告知,本站将立刻处理。联系QQ:16407311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