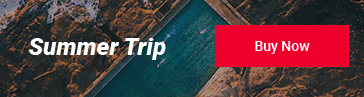中国近代史八大事件什么叫近代史近代史下歌词
信息来源:互联网 发布时间:2023-09-17

在人类历史进入21世纪之际,一场史学在美国悄然兴起。与早期历史学科的革新,如计量史学、文化史、妇女史等甫一出现即引起巨大争论及质疑不同,目前这场史学虽被美国一些极富创新精神又十分有影响的历史学家所接受,并加以发展,但似乎并没有引起多大争议,这就是所谓“国际史”(International history)。目前国际史在美国还只是处于起步阶段,主要被美国一些著名学府特别是哈佛大学为数不多的学者所利用,但其声势显赫,必将在美国及世界史学界掀起巨大影响。
那么,何谓“国际史”?质言之,国际史是一种史学方法。“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这里的“国际史”就是“器”,一种高屋建瓴的广阔视野。因此,国际史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地区或世界史的研究,或外交史甚至国别史的“全球史”研究(Global history),这里的所谓“世界史”、“外交史”、“全球史”,偏重指研究的范围而并非方法。国际史虽然仍在起步阶段,但它已呈现出如下几个特点:第一,彻底打破现今历史研究中的“民族一国家”(nation—state)约束,国际史以整个国际体系甚至文化背景为参照系;第二,强调非、非“民族一国家”因素之作用及影响,如非政府机构(NGO)、竞技体育、瘟疫等在人类进步及历史进程的作用;第三,强调多国档案研究,全球视野的一个基本要素是多国档案及多种资料的应用;第四,国际史强调“自下而上”(bottom—up)的方法,而非如传统的外交史、史之重大人物、政府层面的决策,“文化”因素、“弱势群体”、人类共同的追求等常成为国际史研究的突破口。王国维在《人间词话》里多次提到的古典诗词中存在的所谓“隔”与“不隔”的困境也反映在目前历史研究中。国际史方法恰好能打破这种“隔”与多种分野的局限,因为国际史的追求及旨趣就是要跨学科、踏国别,兼容并包,融会贯通。
国际史最重要的开拓者是哈佛大学历史系教授入江昭(Akira Iriye)。入江昭教授1934年生于日本东京,长期担任芝加哥大学及哈佛大学历史系讲座教席,并曾担任美国外交史史学家协会及美国历史学会主席。长期以来,入江昭大力强调“文化”因素在国际和国际关系中的重要性。早在1978年,入江昭教授在其担任美国外交史学家学会主席的演说中,即以“文化与权力:作为跨文化关系的国际关系”为题,充分阐述文化因素在研究国际关系中的作用。1988年,入江昭教授在其担任美国历史学会主席的演讲中,又进一步强调了国际史视野的重要性,从而为国际史的兴起举起了一面大旗。从此以后,入江昭把“文化”因素纳入其国际史的考量范围。至1990年代,入江昭的国际史学派已完全成型。在入江昭看来,国际关系实际上是一种世界不同文化的交流碰撞关系。如果我们一味看重中国近代史八大事件什么叫近代史、经济、外交关系,可能忽略的是国际关系或人类文明史中最基本的东西。21世纪初,入江昭教授推出了自己国际史研究的经典之作:《环球社区:国际组织在建构当代世界中的角色》。在此书中,入江昭通过研究国际组织来解释近现代国际关系,揭示近代世界的深层国际化进程,为后起之秀提供了可以借鉴和学习的范例。
在入江昭影响下,一批极具影响的国际史著作响亮问世,如哈佛大学历史系教授David Armitage在2007年出版的《作为国际史的独立宣言》就是一例。在该书中,Armitage深入研究作为经典文件的美国独立宣言对世界其他国家的影响。另一位哈佛大学历史系教授Erez Manela的《威尔逊时刻》,则探讨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所提出的新世界秩序设想对埃及、中国、印度及朝鲜等国的深刻影响。Manela目前正通过研究人类消灭天花(Smallpox)的历史来揭示世界的一体化及国际化进程。2008年哥伦比亚大学历史学者Matthew Connelly的《致命的误区:人类控制世界人口的努力》中国近代史八大事件,通过研究19世纪以来世界政府机构、宗教团体、非政府组织、科学组织等在人口控制问题上的政策、主张、建议及冲突,来揭示世界范围内人口控制问题的争论及政策如何影响了世界史进程,甚至是人类未来。2010年,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一本论文集,书名叫《全球的震荡:关于1970年代的(国际)视野》。论文集里的许多作者从各个角度,运用国际史研究方述1970年代诸多事件的国际影响,不少论文属国际史研究的佳作。从这些书籍的出版及其作者的构成来看,哈佛大学历史系(教授及其培养的学生)及哈佛大学出版社显然已成为国际史研究和出版的重镇。
当然,有影响的国际史著作不只上述几本,它们仅是几个有代表性的例子。从以上提到的几本著作的选题可以看出什么叫近代史,国际史研究方法可以运用于国别史如中国史、美国史或世界史研究。那么,如何运用国际史方法来研究与中国有关的重大课题?限于篇幅,这里选取三个笔者认为在中国历史进程中地位重要但长期被忽视或误解的题目作为范例。这三个题目分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一战华工和竞技体育,涵盖国际事件、弱势群体及文化三个领域。
令人高兴的是,国际史研究方法已开始引起华人学者的关注。东华大学的吴翎君教授在著名史学杂志《新史学》(二十二卷第四期)上发表长篇文章《从徐国琦新著 Strangers on the Western Front:Chinese Workers in the Great War 谈国际史的研究方法》,介绍并评论了笔者的国际史研究成果,强调笔者国际史的系列研究“系以‘中国中心’(China—centered)来探究中国国际化(inter—nationa1ization)的轨迹,将中国与一次大战、中国参与近代国际体育活动、华工与一次大战等三大主题,通过多国档案的比较,并加入全球视野,从而将近代中国纳入全球史,既探索中国国际主义的兴起,也说明中国人寻找新国家认同的历史轨迹。整体来看,作者将中国对外关系的老议题,置于中国化(internalization,或译内化)和国际化的双重脉络之中,从更多元的原始史料作探究,进而提出颇具原创性的研究成果”。吴教授认为:“国际史作为研究新法,涵盖跨国或多国的、军事、外交、经济、文化、物质、消费和情感等层面。但不论如何国际史研究必须建立于多国档案和多元材料,一旦脱离档案基础便无法站稳其立论……徐国琦彻底运用多元档案的特色已如前文所述,更重要的是他树立了如何以中国为中心的国际史书写方法,这在过去中西学界的研究中是相当罕见的,诚为其系列著作的最大贡献。”吴教授还身体力行,尝试把国际史研究方法运用到自己的研究当中。她的新著《美国大企业与近代中国的国际化》(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即为此一尝试的优秀作品。
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人类文明发展史上一个重要事件,西方学者的相关研究可谓面面俱到,卷帙浩繁近代史下歌词,但长期以来,很少有人意识到中国人对这场所谓“大战争”或“文明之战”的贡献,以及这场战争对中国历史进程的巨大影响。中外学术界似乎共同认为北洋政府积贫积弱,在国际体系中高度边缘化,且中国内政极其不稳定,“弱国无外交”,因而缺乏改变自身及国际现状的动机及条件。如要打破这种长期形成的认识误区,拨云见月,真正认识中国与“一战”的关系及相关意义,中外学者必须要有下述条件:一需全球视野,要对当时的中外历史及国际关系有透彻理解;二需全面掌握中外档案。显然中国与“一战”关系的研究呼唤国际史的方法。从国际史角度看,“一战”的爆发,对中西文明来说都是一次重大“危机”。这里的“危机”明显反映在这两个汉字的字面上,“危”和“机”,“危”即危险,“机”乃机会也。对中国来说,尤其如此。
众所周知,自鸦片战争以来,英国人凭借船坚炮利把古老的中国强制抛入国际社会。中国从此失去了自己的重心,在完全由别人操纵的一个完全不同的文明体系里,失去自我,无所适从,牺牲了行政、领土与主权,苟且偷生。挣扎于国际舞台上任人宰割的环境之中,中国饱受现存国际体系的欺凌,处于国际关系中的边际地位。西方似乎一直掌握“何为中国人?何为中国?”问题的话语权,并主导对此一问题的讨论。洋务运动是中国人试图扭转这一尴尬处境的最初反应。可惜事与愿违,甲午战争打破了中国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美梦。到19世纪末,中国的处境每况愈下,并因此引起严重的国家认同危机。向西方学习,力争加入西方的认同机制,成为大多数先进中国人追寻的救国方向。1912年,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政体正式退出历史舞台,作为中国传统文明核心价值体现的儒家思想被抛弃,亚洲第一个共和政体在中国建立。这是一个古老中国刻意效法美法的时代。辛亥和中华的建立标志着中国非边缘化努力的新阶段,即由鸦片战争以来的回避西方制度,转为加入西方模式,进而力争加入国际社会,以最终实现中国在国际体系中的非边缘化。
“一战”的爆发有可能让中国化“危”为“机”,使西方人自己把这一对中国不公正的体系打得粉碎,同时因为西方列强穷于彼此厮杀,一时无法对付中国,从而给中国脱去帝国主义的枷锁,整肃内政,寻求新的国家认同及加入国际社会提供了契机。特别是当国际局势分崩离析,现存体系土崩瓦解之时,中国正开始前所未有的改革整顿浪潮。受到现代教育的一大批精英走上历史舞台,如孙中山、王正廷近代史下歌词、蔡廷干、王宠惠、颜惠庆、顾维钧等。这些人学贯中西,明了中外大势,一心利用大战让中国重整山河,成为国际社会平等一员。“一战”期间的中国在文化上、上生机盎然,活力四射,融合了三种波涛汹涌的浪潮:上的民族主义;文化上的打破传统,力争与世界同步;外交上的争取平等,收复主权,成为国际社会平等一员。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使欧洲列强无暇他顾,给身居边缘及不完全独立的中国什么叫近代史,在外交上提供了回旋的余地。为了同欧洲强国争夺国际关系的执牛耳地位,美国的威尔逊总统提出了许多对中国等边缘地位的国家极具力的主张,例如其鼓吹民族自决、公平外交的“十四点”和平计划以及公理战胜强权等很能在中国引起强烈共鸣的言论,也给中国争取打破枷锁、走向国际社会,提供了法理根据。这是中国几千年文明史中,中华民族第一次以西方为参照系来核定自身的地位,以加入一个建立在完全不同的文明基础之上的国际体系。
所以“一战”的爆发可谓积贫积弱的文明古国脱胎换骨的天赐良机。传统史学强调“一战”带给中国的“危”,但忽视“机”的存在,国际史的国际视野正好帮助我们看到了被长期遮掩的“机”。正是从国际史的角度,拙著《中国与大战》大力强调“一战”的双重意义 :一是因为中国的积极参战介入,古老的中国让所谓的“大战”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大战;二是因为“大战”的爆发,大战的影响,大战成为中国历史一个极其重要的部分。因为中国的参战,中国得以参加巴黎和会,得以派出一流外交家如顾维钧什么叫近代史、社会活动家如梁启超等到巴黎,第一次向世界提出中国的平等诉求,表达中国作为平等一员加入国际社会的愿望,展现中国人不卑不亢、有理有节的外交风范。国际联盟的宪章里有许多中国人的观念,中国代表团甚至捐弃前嫌,着眼大节,支持日本在巴黎和会提出的“种族平等”的创议。也许有人说,中国在巴黎和会失败了,但我们不要忘记,恰恰因为“一战”激起了中国人高度的民族自尊心,并由此提出了加入国际社会作为平等一员的强烈诉求,才导致中国人对巴黎和会寄以无比巨大的期望,由此产生了所谓的巴黎和会失败情结,造成极强烈的民族刺激,结果导致五四运动的大爆发。无论从何种角度来说,无论是广义或狭义,五四运动都是中国近代历史进程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是中国人寻求新的国家认同及国际化的一个里程碑。奇怪的是,多年来很少有人把五四运动同“一战”联系起来。如此论可以成立,我们甚至可以质问:“没有一战,何来五四?”
前面笔者用了“所谓”的巴黎和会失败,事实上笔者认为巴黎和会并没有失败,不仅仅因为代表战后国际新秩序的国联宪章有中国人的积极参与,不仅仅因为这是第一次在一个极其重要的国际舞台上中国发出了清晰、雄辩、合理的民族诉求和民族独立的声音,更重要的是中国义凛然的抗争,把日本逼到世界的被告席。是的,《凡尔赛和约》把山东转让给了日本,但就是中国人在巴黎和会发出了正义诉求,迫使日本在1922年把山东还给中国。正是由于中国人拒绝在不公正的《凡尔赛和约》上签字,才得以让中国在1921年同德国签订基于废除不平等条约追求之上的第一个平等条约。事实上,正是由于中国参战,中国早在战争期间就得以收复与德国之间的治外法权。凡此种种,难道我们可以说中国在巴黎和会上失败了?
质言之,从国际史角度,我们可以得出中外史学界迄今无人提出的性结论:中国与“一战”关系意义非凡!中国与“一战”的互动标志着中国人真正意义上寻求国际化及新的国家认同的开始。“一战”让中国踏步走向世界,同时也把世界带到中国。
如果上述论点是从全球视野、多国档案来透视中国与“一战”关系得出的结论的话,那么,通过“一战”华工角度自下而上透视中国与“一战”的关系,则可以描述更为明晰的中国与世界接轨及参与重建西方文明的精彩历史,并可进一步解释中国精英和西方列强如何利用华工来实现各自的宏伟大业。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14万华工在英法两国政府的征召和中国政府的安排下近代史下歌词,远涉重洋,作为苦力来到战火纷飞的欧洲,为协约国集团的所谓“文明之战”贡献“苦”与“力”。这是人类文明史上东西方交流的重要章节,但长期以来,中外学术界对他们的“旅程”不甚了了。我们不知道他们在中国历史进程中的地位,也不明白他们对那场大战所作的贡献,他们在中国历史及世界历史上的地位又是如何。无人解释这些华工虽然来自中国,但他们的历史却属于整个世界。在许多人眼里,“一战”中抵达欧洲的14万华工也许是苦力,的确,在欧洲,在旅途,他们确实吃尽了苦,出尽了力,甚至牺牲了生命。也许他们去欧洲的主要动机是为了谋生,但是,从国际史的角度,他们的旅程明显与中国及世界的命运密切相联。我们甚至可以说,他们是中国放眼走向世界,主动加入国际社会的先行者。正因为他们的存在,正因为他们可歌可泣的旅欧经历,中国的精英们才可以在巴黎和会上义正词严地要求国际社会还中国以公道。正因为华工源源不断地到来,英法诸国在大战之生死关头,才可以免去人力资源破产的后顾之忧。重要的是,这批华工是远瞩的中国志士仁人在世界格局重新洗牌的转折关头实施的“以工代兵”策略及国家复兴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民族精英们殚精竭虑地思考中华民族如何走向世界的时候,这一批任劳任怨的中国农民,赴汤蹈火,担起了挽救国运的重责大任。正是精英阶层与下层大众的有机结合,通过“一战”华工的光荣旅程,才让中国得以在“一战”期间谱写了一曲中西交流的辉煌篇章。华工们得以参与拯救中国与西方文明于水火的重要使命,使饱受战火煎熬的欧洲得以一睹华工风采,让世界得以第一次面对面地了解和感受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坚强及智慧。
因此,“一战”期间中国的“以工代兵”策略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有胆识、有目的、有远见地加入国际社会的开端,是东方大国参与拯救西方文明的中外合作大事件。更为重要的是,14万华工不仅仅是14万士兵,无疑也是中国的14万使者。1918年在美国出版的《中国学生月刊》就直截了当地写道:“赴法华工实乃中国派往世界的信使。”教青年会在“一战”后的一篇报告中说:“一战的爆发导致东西方文明的直接交融,是此次大战争的一个最令人称奇的经历。”华工最重要的贡献不仅体现在他们参与对西方文明的拯救,更体现在他们在中国以全新的姿态进入国际社会及中国人寻求新的国家认同的过程中扮演的举足轻重的角色。
“一战”华工第一个突出贡献在于他们为中国直接宣战提供了机会。早在1914年秋及1915年,中国政府即两次强烈要求参战,以便化危为机,但先后被英国及日本拒绝。由于这个背景,中国只好“明守中立,暗事参加,并决定以工代兵”。当德舰击沉运送华工的商船导致数百华工葬身海底时,对中国参战鼓吹最力的梁启超指出,“我国既为国际团体之一员,则在体面上及责任上,对于德国此种蔑视中立国之行动,万难漠视,否则,即为自外于国际团体之列”。“故我国一方面以国家对于国民之责任,一方面对于世界国家地位,尤不得不有一种主张也”。他提出,中国如能借此参战,“实为我中华国政上开一新” 。由此可见,华工不仅为协约国作出了宝贵的贡献,还出色地捍卫了中国的国家利益,为中国争取参战起到了关键作用,并为中国战后参加巴黎和会及国际事务提供了机遇。
华工的第二个突出贡献是教育了中国的一批精英。鲁迅曾经写道:“欧战时候的参战,我们不是常常自负的么?但可曾用《论语》感化过德国兵,用《易经》咒翻了潜水艇呢?儒者们引以为劳绩的,倒是那大抵目不识丁的华工。”蔡元培在1918年的一个演说中宣称,此次大战,“我国为参战之员,若供给原料,输送华工,皆我参战所尽之义务,故中国在国际上亦应该处平等地位”。康有为在致中国出席巴黎和会代表团团长陆徵祥的信中强调,“窃以中国今者之参预协约大庆成功,举国若狂”,“惟吾国真有功于欧战者”,实乃华工之力。“吾国参战之功,惟工人最大,则我国所争议约之事,应以保护华工为最大事焉”。他建议中国以此为契机,同各国谈判,争取华工在外国的平等地位。晏阳初后来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中国在巴黎和会的地位,不是外交家的辞令换来的”,而是“被中国人轻视被外国人践踏的苦力争来的”。
“一战”华工的第三个贡献是他们成为中华建立以后中国参与国际社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早在一开始,中国政府即把欧战华工与中国的未来发展及在国际上的平等地位联系起来。如早在1916年,中国驻法公使胡惟德即建议政府要力争华工在法国的平等地位。元老李石曾、吴稚晖,以及蔡元培、汪精卫等人都力主华工出洋,并利用出洋华工改造中国社会。所以“一战”华工成为这些社会精英社会改革的重要实验品。蔡元培明确指出,如果中国想提高自身的国际地位,了解西方文明势在必行,“在欧华人就是中国学习西方文明的前驱”。从这个意义上说,“一战”华工不仅成为中国学习西方文明的先行军,更是后来留法勤工俭动的楷模。周恩来在1921年写道,“一战”华工来法系“勤工俭学”运动的前奏。青年也曾考虑以帮助在法华工的途径到法国勤工俭学,并对华工寄予厚望。当时曾和友人讨论道:“我们不妨把华工集合起来,鼓励他们念法文,学习技能以及了解一下法国的社会组织。那么,他们返华后,便能在下层阶级成为改革运动的中坚分子。在这些华工中我们可以为改造中国的伟业找到很多同道。”
当时一批社会精英为了把华工变成改造中国的重要力量,殚精竭虑,献计献策,并身体力行。1917年李石曾在巴黎创办《华工杂志》,专门为华工提供有用信息及教育之用。蔡元培创办华工学校,并亲自编写讲义,其中包括德育30篇、智育10篇。蔡元培的讲义强调“合群”,“舍己为群”,“尽力于公益”等。汪精卫指出,蔡元培的这些讲义“一在保全华工固有之美德益发挥而光大之,一在修补华工向来所不免之缺点,曲喻而善之。以先生平日之人格与学问,所修养者至深,故其所言,简而深,平而切。工余读之,身体而力行之,则道德与智识,不期而日进于光明。此诚华工淑身之本,而自立之源也”。这里蔡元培的教学理念同其在1916年与李石曾等发起的华法教育会是一脉相承的,都是旨在扩大中外文明交流,寻求中国新的国家认同。该会的目的约有四端:一日扩张国民教育,二日输入世界文明,三日阐扬先儒哲理,四日发达国民经济。晏阳初为“一战”华工创办《华工周报》也是抱着同一信念。该报旨在帮助华工学习,启迪华工心智,培养华工自尊自爱、爱国爱家的情操,要求华工“思身,思家,思国”近代史下歌词。《华工周报》上的文章都着眼于开阔华工的思想境界,加强他们的国家、民族认同及爱国热情。
在政府的新外交政策指导下,在众多中外人士的帮助下,在教青年会的照顾下,这些华工中许多人不再是昔日的“吴下阿蒙”,他们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国家观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从前的中国对华工来说,充其量不过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但是中国现在与他们密切相关,他们代表中国。来自山东平度的一位华工傅省三在其参与《华工周报》征文并获奖的《华工在法与祖国的损益》一文里说,华工在来法之前根本不明白个人与国家的关系,不清楚家庭与国家的关系,但是,当华工目睹了欧洲人在战场上为了国家拼死打仗时,华工的民族主义及爱国主义感情也因此被激发出来。他写道:“一到阵前,看见外人为国为家牺牲性命,自己不自不觉地就生出一番爱国爱家的心来。”这篇文章还提到许多华工决心用他们在欧洲学到的新知识来教育国内的同胞,“从前华工只知道女子缠足为美”,“现在既看见西洋的女工、女农、女医等”,因为天足,可以与男人并肩工作、劳动,才意识到从前的想法错误。将来回国后,定要改掉旧日的恶习,用从洋人那里学来的新知识、新思维开导国人,改造社会。傅氏甚至写道,从前认为中国人不如洋人,今日与他们赛脑力体力,“方知他们不比我们高。若回祖国再加以教育,敢望将来祖国的进行(步)”。傅氏开始相信中国人完全可以建立一个同西方并驾齐驱的新中国。傅省三还写道,“现在和平会一立,竟将中华天朝大国的名目取消,列在末尾”,“并不准我国有发言权,华工经此番的淘汰激励近代史下歌词,如梦方醒,忽然就发起爱国心了。这种思想是来外国而有的。若不来法国中国近代史八大事件,恐怕仍在中国做梦”。
许多华工来到法国后开始特别关注祖国的命运,感同身受中国的民族危机意识,关注中国的国际地位,并且愿意为祖国出力。外交部华工事务员李骏在1917年12月份的华工通告中发出倡议:“数月来,祖国北京直隶有些地方,惨遭天灾,民不聊生,希望华工发扬爱国爱同胞的热血心肠,慷慨解囊,为祖国捐款。”通告借此鼓励华工爱国思想。李骏后来在外交部的报告中也写道,“华工中知大义者不乏其人,互相鼓励,争先恐后”捐款,多者一人独捐200法郎,少者1法郎,此次义捐共收到16,230法郎。当华工从《华工周报》上得知中国在和会上不能收回山东时,许多人纷纷上书谴责列强,并踊跃捐款,支持政府维护国家利益。一位叫邰魁义的华工捐款30法郎,希望政府用来振兴工业。有一位华工把他积攒两年的全部工资捐给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团,要求他们用这笔钱做任何对中国有利的事。类似的爱国举动不胜枚举。
华工的高涨爱国觉悟也体现在他们自觉维护国家尊严上。当美国总统威尔逊在赴巴黎参加和平会议的途中经过法国哈佛港时,当地的华工主动派出代表欢迎威尔逊。为了庆祝“一战”胜利,在比利时的英军特开协约国部队运动会,并邀请华工参加。12队华工约6000人来到会场。他们发现在空中飘扬的多国国旗中独缺中国国旗,认为这是对中国国家尊严的侮辱,于是当即离开运动场以示。翻译顾杏卿、夏奇峰等亲眼目睹华工这一爱国壮举。当获悉列强达成对华不平等的《凡尔赛合约》时,华工派代表致书陆微祥,并置一于内,“苟签字承诺日本之要求,请即以此枪自裁,否则吾辈必置尔于死地”。华工在回国途中,当轮船停靠在日本码头时,船上的华工坚决拒绝上岸,他们宣称日本对中国一向不厚道,作为中国人,他们不应该登上日本国土,去贪图享乐。
华工在回国后,许多人开始为建立新中国而献智献力。曾担任华工译员工作的刁敏谦写道,归国的华工个个都充满着新精神,“毫无疑问,这些归国的华工找到了传播他们所信奉的新思想的沃土”。部分华工回国后组织归国华工工会,要求提高工人的权利。该会工人誓言不赌、不嫖、不酗酒、不抽鸦片。该工会是中国最早的现代工会之一。这些归国华工是改变中国命运的一支生力军。在20世纪20年代前期,中国工人经常举行各种,这些归国的华工也因此被人指控说:“中国劳动界的煽动者都是那些来自欧洲战场的归国华工。”在有些政府部门,归国华工甚至被称作危险的布尔什维克潜藏分子。著名的五四运动史研究专家周策纵指出,在五四时期,那些归国华工在欧洲的经历使他们在上海工会的组织化以及活动中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他们“有力地促使五四运动在20世纪20年代早期向社会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极端方向发展”。周氏认为,新式工人运动的基础是“民族主义而非布尔什维克主义”。华工的爱国热情还体现在其积极创新上。1924年2月,美国人富路得(Carrington Goodrich)在北京会见了一位来自直隶通县的农民。此人“一战”期间曾在法国做工,回国后积极研制一项机器发明,成功后请富路得介绍专家鉴定一下。富路得的两位工程师朋友认为该发明除若干枝节处需修正外,其余都正确。该华工在写给富路得的信中说,他钻研发明,目的是为了响应《华工周报》的呼吁,把其自法国期间学习观察的心得“带回中国传布给同胞”。山东博山和尚村的孙干怀着考察教育的目的,参加华工队伍,回国后写有《欧战华工笔记》、《世界大战战场见闻记》两部书稿,意在向国人传播他在法国的所见所闻所思。另一位华工所写的《夏雷日记》更是记载华工对国际关系和国家命运的思考及观察。“一战”留在法国定居的华工当然一如既往充当传播中国文明的使者与桥梁,有些甚至直接参与影响中国前途的活动,如山东潍县一位华工战后留在法国,以开茶馆为业,多次为周恩来在法国的活动提供方便。
最后应该指出的是,当时的北京政府很想充分利用归国华工为国家服务,为寻求中国新的国家认同及国际化出力,因此在1919年8月18日令侨工事务局拟出安置华工章程。各地华工交涉员也出于对华工的参战贡献之感佩,在政府的指示下,力图妥善安排归国华工,“何忍听其失所,流而为匪”。可惜的是,由于军阀混战,社会动荡,归国华工并未得到重用。其中有些人由于生计等问题甚至沦为土匪。例如1923年山东临城劫车案中,即有“一战”后由法归国华工参与。尽管如此,我们对欧战华工的贡献及历史地位不容低估。
更重要的是近代史下歌词,在政府及社会精英利用改造华工来改造中国的同时,华工亦明显地影响了中国社会精英的价值观及对国家前途的新思维。首先,如前指出,华工的一些经历明显影响社会精英对下层人民的态度,使他们意识到劳工的伟大。如蔡元培在1918年11月16日庆祝“一战”胜利的系列演说中提到,“一战”积极意义重大,是光明的主义战胜黑暗的主义。他说:“但是我们是四万万同胞,直接加入的,除了在法国的十五万华工,还有什么人?这不算怪事!此后的世界,全是劳工的世界啊!”蔡元培因此喊出“劳工神圣”的口号。李大钊也宣称,“一战”之后的世界,“变成劳工的世界”。“一战”的胜利,是“庶民的胜利”。晏阳初由美国到法国为华工服务过,与华工朝夕相处的经历,改变了他的一生。晏阳初后来说,“欧战我参加服务华工”,“与其说我们到法国教育工人,还不如说工人教育了我们。……于是,我在华工营就下了一个最大的决心:愿把自己献身于苦力,以前的‘小我’死了,以后的‘大我’就是‘苦力”’。他坦承过去对劳苦大众甚至中国国情都不太了解,“岂知到了法国,苦力教育了我,认识了苦力的伟大,随而真正认识了中国”。与华工相处,使晏阳初意识到中国农民的“苦不堪言的苦”和“力大无比的力”。他下决心要用一生“解除劳工之苦,开发苦力之力”。从此晏阳初决心致力于平民教育,并最终成为享誉世界的平民教育家。通过在法为华工服务的经历,晏阳初认为他找到了救国良方,认为只有实行平民教育,并从社会基层改革做起,中国才有机会复兴,才有资格成为国际社会平等的一员。他要为中国“除文盲”,“造新民”,进而提出了“三C”救中国的说法,即Confucius(孔子),Christ()和Coolie(苦力)。1949年后,晏阳初将其视野扩大到全世界,要“除天下文盲,作世界新民”。他的救国救民理念由中国走向世界,变成中国国际化的组成部分了。
如果说从国际史角度研究中国与“一战”关系可以证明中国对“一战”的贡献及“一战”对中国历史进程的重大影响,如果说从被中国人及西方人双重遗忘的“一战”华工角度,我们能够明嘹所谓“苦力”在“一战”中为中国及西方文明的发展作出的巨大的“苦”与“力”,并能从自下而上(bottom—up)的角度全新解释中西文明交流及理解中外历史的话,那么,从人类竞技体育角度特别是奥林匹克运动的视野,我们可以分析中国寻求国际化及新的国家认同的另一个全新的历史轨迹。体育属于大众文化范围,国际竞技体育也是人类文明相互交流及展示彼此“和而不同”的重要平台。现代体育特别是现代奥林匹克运动因此成为近代中国走向世界、积极参与国际社会的一个重要途径。通过近代体育,我们可以研究几代中国人如何利用西方体育来改善中国的命运,重塑国家认同,提高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
现代奥林匹克运动的兴起与近代中国寻找新的国家认同及国际化的开端几乎同时。1894—1895年间的甲午中日战争中国惨败,从此让中国人从四千年大中国梦中觉醒,一些先进的中国人开始意识到中国根本不是什么所谓“天朝大国”,而是“东亚病夫”;可以说19世纪的中国人从头到脚,从里到外都出现问题。男人头缠长辫,几百年来汲汲于科举考试,满脑子孔孟之道,以白面书生、四体不勤为荣,头出现了问题,阳刚气尤显不足。中国女人从明清以降,以三寸金莲为美,以弱不禁风、一步三摇为自豪,裹脚的风俗不仅导致近半中国人的脚出了问题,甚至近半中国人属于残疾之列。病态的男人与残疾的女人,必然导致病态的国家。严复、梁启超、张伯苓等先哲开始大力鼓吹中国人要向西方学习,根治中国人的头脚痼疾,重塑国人形象,寻找新的国家认同,以西方为目标的国际化进程在中国开始启动。这一巨大的思维变化,为中国人接受西方思想及体育理念打下良好基础。
就在中国甲午战败,人心思变的同时,1894年现代奥林匹克运动在法国问世。两年后第一届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在雅典举行。奥林匹克运动最先被介绍到中国,与教青年会(Young Men’s Christian Association)密切相关。1895教青年会首次在中国的天津市设立分会,并大力推广西方体育。篮球、排球等现代体育竞技运动一一被引进中国。后来的天津南开学校校长张伯苓之成为中国奥林匹克运动的先驱,被当代中国人炒得沸沸扬扬的所谓“奥运三问”之所以出现在天津,都跟教青年会天津分会密不可分,甚至近代几乎所有中国的体育领袖都或多或少地与教青年会有关。中国之所以在1922年成为国际奥林匹克大家庭之一员,同年王正廷成为首位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之中国委员,1910年开始的全国运动会之所以能坚持下来,凡此种种,都与教青年会的领导及参与密不可分。这同时也说明了中国的奥运情结从一开始就是与其国际化进程相关。换句话说,中国参与现代奥林匹克运动归根到底是其寻求国际化的产物。
中国最早的关于奥林匹克运动会的系统介绍书籍,即用“我能比呀!”作为标题,该书作者宋如海(教青年会干事)在介绍1928年阿姆斯特丹奥运会时,用“我能比呀!”翻译Olympia,可谓既传神又得体,充分反映中国人希望被外人承认及走向世界的迫切心态。1932年中国第一次参加奥林匹克运动会更是与国际有关。中国最初本无计划派运动员参赛,但有关日本可能借满洲国的名义参赛来变相使满洲国在国际社会合法化的消息,让许多中国人义愤填膺,并最终促成刘长春1932年单刀赴会洛杉矶奥运会的壮举。
1979年北京重返奥林匹克运动及其他主要体育家庭后,利用体育向世界展示一个开放的新中国,力图用奥林匹克金牌数来证明中国是强国,不是东亚病夫,值得世界的尊重,并向国际社会展示中国新形象。金牌至上,举国体制,“国内练兵,一致对外”成为1980年代后中国体育的新。但这一同20世纪初“奥运三问”的背景是一脉相承的。国际化的真谛首先是中国化,中国化是国际化的终极目标。在距1907—1908年的百年后,中国人终于实现“奥运三问”所有目标之际,该是重新审视检讨百年中国国际化轨迹,重新思考适合中国国情的新的国家认同的时候了。我们该集体思考什么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天命,什么是中华民族的天命,什么是我们所有中国人的天命。只有对天命有了清晰的定义后,中国的国际化才不会继续走弯路,中国人才会真正站起来,才会真正成为体育及强国。
质言之,中国近代体育的“奥林匹克之梦”同几代中国人如何利用西方体育来改善中国的命运,重塑国家认同,及提高在国际上的地位密不可分。1907—1908年间中外人士共同提出的“奥运三问”实际上并非着眼于中国的体育竞技实力,而是侧重于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国际生存能力。从晚清到,再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百年问,一条清晰的主线就是,体育在中国的化。自1895年甲午战争中国惨败于日本之手及教青年会同年在天津建立中国首个分会后的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人一直以西方的国家认同体系及价值观为参照系和依归,意欲通过参与奥林匹克运动等各种方式加入西方主宰的国际体系即为明证。在很大程度上受教青年会的影响,先进的中国人开始关注现代奥林匹克运动,并把引进西方体育同救国强种,寻求新的国家认同联系起来。在1907—1908年间,他们公开提出中国何时可以举办奥运会的问题。一百年过去了,几代中国人的世纪奥运会主办梦终于在2008年得以实现。2008年可谓中国人百年奥运梦的圆梦年,也是百年中国人追求国际化的巅峰时刻。利用国际史的视野和竞技体育这一角度,我们可以透视中国近百年来尝试回答“什么是中国,何谓中国人”这一命题的独特历程。
前节分别从华工、“一战”及体育三个角度展示了从国际史来研究中外关系及中国近代历史的新视角及所得出的新结论。这三个题目明显反映出国际史的特质:其一是国际视野,其二是跨越“民族一国家”的分析框架,其三是侧重小人物、文化层次及“自下而上”的研究方法。除了要具有深厚的学术根底,国际史研究方法最重要的成功保证是多国档案、多种资料的应用。真正的史学家都明白史料的重要性。傅斯年的名言“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胡适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王国维的学术“三境界”说,都体现了前代大师们对史料的重视。国际史方法在史料运用方面强调的是全球视野下多国档案及各种官方及民间资料的运用。以上述三个选题为例,笔者为研究中国与大战这一课题曾遍访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研院近代史所档案馆,美国、法国、英国及德国档案馆、图书馆等,仅查档时间即耗时一年有余。
笔者在意图利用体育来研究中国的国际化及寻求新的国家认同时,为了解决所谓中国人的“奥运三问”这一被广泛误解的命题,全面披览了藏在明尼苏达大学教青年会档案馆的相关资料。为了解决乒乓外交的前因后果,除遍找所有中外官方档案外,还查阅了收藏在密西根大学历史档案图书馆的所有当事人的口述史及回忆录。“一战”华工研究也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受益于多国档案及多种资料。拙著《西线战场的陌生客:华工与第一次世界大战》主要取决于来自上述国家的许多从未被人利用的资料。例如书中研究“一战”华工与加拿大的关系,就是得益于加拿大档案馆的档案。书中涉及的华工在欧洲的生活及贡献方面,资料主要来源于教青年会档案,以及法国、比利时什么叫近代史、英国、美国、中国等官方和民间资料。其中特别受惠于本人多年追寻的私人资料,如当事人日记、通讯及回忆录等。正是因为最广泛地占有资料,本书才能辟专章来研究华工与美国、华工与中国精英互动、华工与法国妇女之关系等新课题。
作为国际史,不仅要有全球视野,全面熟悉世界学术界的相关研究,更重要的是利用多国档案,各种资料。只有做到这些,才能达到王国维先生所述治学三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以及“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一代史学大师陈寅恪先生自述“平生为不古不今之学,思想囿于咸丰、同治之世,议论近乎湘乡、南皮之间”。如果我们可以套用陈先生的这一议论来解释国际史的话,那么,所谓国际史就是“不中不西之学”,议论近乎司马迁及兰克之间,即效法兰克,充分重视史料的价值,力求达到司马迁的“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报任安书》)的境界,并最终达到林语堂先生所说的“两脚踏东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的目标。多年以来,国内外学术界由于受到学术分野的限制,治中国史的难以兼及世界史,研外交史的很少顾及社会史、文化史,更由于受到语言的限制,史学研究令人有“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或“一叶障目,不见泰山”之感,故国际史方法如运用得当,使用者训练有素,理当有“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之气势,以及“柳暗花明又一村”之妙。
在目前中国国力全面提高之际,如何提高中国学术研究水平特别是历史研究水平,是我们中国学者必须面对的一个迫在眉睫的挑战。笔者不揣寡陋,草成此文,旨在与所有关心中国国际地位与提高中国学术研究水平的志士仁人共勉。得失与否,尚祈方家教正。
免责声明:本站所有信息均搜集自互联网,并不代表本站观点,本站不对其真实合法性负责。如有信息侵犯了您的权益,请告知,本站将立刻处理。联系QQ:1640731186
 1
1
 0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