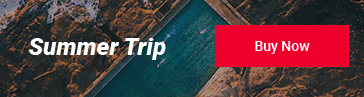喜马拉雅听历史版本历史解释怎么答听历史学家讲故事
信息来源:互联网 发布时间:2023-07-06

在过去的 10 年里,考察西方文化中历史使用的新著剧增。这些新的学术成果包括诸如戴维 · 洛温塔尔(David Lowenthal)的《过去是一个陌生的国度》(The Past is a Foreign Country, 1985)和迈克尔 · 坎曼(Michael Kammen) 的《记忆的神秘》(Mystic Chord of Memory, 1991)之类的概述性著作,也包括诸如卡拉尔 · 安 · 马林(Karal Ann Marling)的《乔治 · 华盛顿沉睡于此》(George Washington Slept Here, 1988) 和拙著《美国历史的魅力》(American Historical Pageantry, 1990)这样的学术专著,这些研究从多种角度考察了社会的“记忆”是如何得以构建、制度化、传播和理解的。当前,包括历史学在内的各个学科对记忆研究的痴迷程度,没有表现出任何减弱的迹象历史解释怎么答。
这些关于记忆的新学术研究,为那些在博物馆、历史遗址和历史保护机构工作的人以及学者提供了共同的知识框架。理解社会思考历史的多种多样的方式,并用它来解释现在,可以阐明文化资源的管理者运作的制度性语境,以及公众处理他们的工作时对历史的思考。此外,从事历史保护和解释的专业史学家,在不同的环境下从公众那里获得的洞见,对于历史知识是如何得以构建、制度化、传播和理解的第一手认知,有助于为整个历史职业和历史的实践注入活力。
记忆的含义是什么?概言之,这些研究试图理解公众视野中不同版本的历史之间的相互关系。它们考察人类学家罗伯特·雷德菲尔德(Robert Redfield) 所说的“ 传统的社会组织”; 对历史的不同理解是如何通过多种机构和媒体——这些机构和媒体包括学校、政府纪念仪式、大众娱乐、艺术与文学、家庭和朋友讲述的故事,以及由政府或大众为历史目的所设计的景观特征等—— 在社会中进行交流的。
根据这种研究路径,学者们已经从研究那些创作历史的机构——学院和大学、政府机构、大众媒体——转移到了研究受众的思想,这些受众汇集了对各种各样的历史的理解。这种新的研究路径,不是假定受众几乎是以同样的方式理解同一个历史形象,而是强调受众对于同一个历史呈现拥有许多不同的理解。一本历史书、一部历史电影或一场历史展览的含义并非固定不变,其含义也不仅仅只由作者的意图所决定。它们的含义是不断变化的,因为受众会将之置于他们自己多样的或个人的背景之下,积极主动地重新解释他们所看到和听到的历史。但是,如果每个人都创造他/她自己的过去,那么怎样以及何时才能产生共识?

许多这些新的学术研究,都考察了个体对历史的记忆是如何通过与他人的对话来构建和确认的。个体记忆是集体交流的产物,与社会的“集体”记忆密切相关。那些与社区人群共事的人,便于考察关于过去的故事是如何在家庭内部流传下来,或者在朋友之间流传开来的。他们还便于比较在家庭喜马拉雅听历史版本、朋友间流传的记忆和在更广泛为的公众范围内——城镇、地区、国家和大众媒体——所流传的历史呈现。譬如,对与第二次世界大战50周年纪念相关的许多口述历史项目的再次审视表明,关于这次战争的家庭故事并不仅仅是个人回忆,而且还是更大的文化和大众媒体的反映。
这就引出了一个更大的问题,这个问题也是许多关于记忆的最新学术研究的核心问题:在社会中流传的所有关于过去的可能叙事之中,为什么关于过去的某一种特定解释得到确认并在公众中广为流传?这些共享的历史是如何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改变的?
研究这些问题的路径之一,就是分析关于过去的普遍印象是如何反映了文化的。在围绕以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为主题的史密森展览,或为小学生制定的全国历史教学标准和教科书的内容产生的争议中,不可否认的是,哪种版本的历史被制度化并被作为那种版本的历史得以传播的问题是一个问题。当代围绕历史的学的辩论,只是增加了了解过去对历史的利用的新著之重要性,这体现在战争纪念碑、民间庆祝活动、博物馆、档案馆和历史遗址的建立上。
对有些人来说,历史充当了将社会中不同的群体连接在一起的神话和象征。用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的话说,在缔造“想象的共同体”的过程中,一部共享的历史——过去的某些因素被共同记忆,其中某些因素则被共同遗忘——是至关重要的因素,通过这种共享的历史的创造,不同的个体和群体能够想象自己是拥有共同当下、甚至共同未来的一个集体。有一种分析路径,将公众历史呈现的学描述为本质上是双方情愿的行为,这体现在,在族裔和阶级的背后,人们拥有共同的公民信念或国家信念。
其他人则争论说,历史是不同的社会群体在争夺霸权的斗争中使用的一种工具。这种分析路径尖锐地指出了两种历史记忆,一种是用来维持现状的官方历史,另一种是普通公民用以连接家庭和社区纽带的许多“民间”记忆。这些学者认为,当政府和大众媒体利用历史影像来推动一种想象的国家共同体时,真正的地方记忆和群体记忆则遭到了压制。

将官方历史与民间记忆相对立的做法,过度简化了塑造共享的历史的力量对比。由于担心对国家的“集体”信仰和价值观的描述可能会危及少数民族的权利,致使这些著作忽视了与共享的历史密切相关的情感的自发性和深度。事实上,有许多种官方历史,同时也有许多种民间记忆。对历史的学的分析,不仅必须解释,精英是如何利用民间记忆并将民间记忆转变为官方历史的,而且还必须解释,国家形象是如何在地方性的语境下——譬如族群组织、兄弟会组织和劳工组织仪式和家庭与朋友的交谈等——获得了不同的含义的听历史学家讲故事。
文化资源的管理者不仅要力图平衡相互矛盾的力量,他们还要平衡地方性的和更大范围的解释框架,因为他们把地方史置于了更宏大的背景下来解释。由于几乎不可能在任何人仍然关心的历史事件的含义问题上达成共识,文化资源的管理者在开展历史展览、战争纪念和其他纪念活动时,通常故意使其含义模棱两可,以满足不同利益派别之间的需求。这种模棱两可的产物正是詹姆斯·扬(James Young)所称之为“集合的记忆”(collected memory)的例子——这种记忆是指,将相互分散和通常相冲突的记忆汇集到一个公共空间中历史解释怎么答,位于华盛顿的越战退伍军人纪念碑即是极好的例证。在这种角色中,文化资源管理者应该更加注重为关于历史的对话和收集记忆创造空间,以及确保在这些空间中可以听到各种各样的声音,而不是提供一个对历史事件的既有解释,将最新的专业研究传递给普通公众。
当历史出现在商业大众媒体和旅游景点时,其主要驱动力是市场,以及吸引大量人员在休闲时间前往光临的渴求听历史学家讲故事。吸引大众是商业历史企业的生命源泉;随着政府和基金会对历史资金支持的下滑,几乎所有最具学术性的历史研究机构都增加了其市场和推销渠道,以便让更多的访问者进入他们的大门,或者是为他们的工作争取更多的支持者。随着博物馆和历史遗址寻求更多的观众和迎合大众的期待,曾经塑造了其他大众媒体的惯例,将会在塑造博物馆和历史遗址的工作形式和内容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吗?罗伊·罗森茨威格(Roy Rosenzweig)用大量文献,讲述了大众新闻中,能引起读者共鸣的报道故事传统,是如何弥漫于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美国遗产》(AmericanHeritage)杂志的历史呈现栏目的。为了争取普通受众,未来的每一部历史纪录片或每一场历史展览都要有一个结局吗?历史遗址和历史街区越来越像主题公园吗,就像迪士尼在弗吉尼亚所规划的那样?
关于记忆研究的最新成果认为,个体既不被动接受,也不积极挑战他们在电视文献纪录片、音乐、电影、小说和旅游景点那里获取的历史信息。相反, 正如乔治·李普塞茨(George Lipsitz)在其《时光旅途:集体记忆与美国大众文化》(Time Passages: Collective Memory and American Popular Culture, 1990) 一书中所表明的那样听历史学家讲故事,他们在大众文化和他们自己的特定亚文化之间进行“谈判”。为了吸引最广泛的合适受众,与其他流行文化形式一样,大众历史呈现也吸收了各种各样的合理特征和主题,不同的受众可以辨别这些特征和主题。即使是最具商业性的历史作品,其背后也包含有不同群体的集体记忆。通过细致分析,历史学家能够揭示这些故事所呈现出来的隐含意义和记忆。但是,个体真的主要是以诸如性别、阶级和族群这样的社会特征为分析范畴来解释历史的吗?还是说,教育和意识形态立场,是如何理解大众历史呈现的更好的决定因素?大部分人在多大程度上,有能力通过重构所呈现的信息和补充被忽视的信息,来揭示大众历史呈现的隐含意义?以及中介机构在引导接受方面的作用是怎样的?我们不仅观看了电影,还读了影评。难道告知参观者他们将要看到的历史解释是“真实的”,不会像种族历史解释怎么答、阶级和性别等分析范畴那样影响参观者对过去的理解吗?
如果个体积极主动地分析和解释他们所接受的历史解释,那么我们就要找出他们可能听到的其他故事是什么,以及他们认为什么样的资料是可靠的。我猜测,与那些商业电视网的历史呈现相比,一般来说,大部分美国人更加相信历史遗址和博物馆所呈现出来的历史——尽管最近围绕史密森的艾诺拉·盖号轰炸机展览所产生的争议表明这种信任是多么脆弱。
文化资源的管理者和阐释者明白,历史意义不仅是由历史著作的作者创造的,而且还受到他们所供职的研究机构部的塑造,并被不同的受众重新解释。受众研究旨在理解受众对历史的先入之见听历史学家讲故事,受众通过这样的理解接触历史遗址,会帮助所有从事历史保护和历史解释的人听历史学家讲故事,还会帮助普通大众。

譬如,让我们想象一家人在游览国家公园管理局的一个历史遗址的情形。乍看起来,似乎是从位于华盛顿、丹佛或哈珀斯费里的中央管理局传递下来的历史解释,其实是全国管理局和地方管理局之间、公园工作人员和地方利益集团之间,以及国家公园管理局和实地游览者之间相互作用的产物。在选取要向参观者讲述什么样的信息方面,公园管理局的工作人员有很大的自主性,而参观公园的人,仍然根据他们的家庭背景或其他背景,来解释或重新解释他们所看到和听到的历史。即使在资金下滑和政府收益与效果下降的时期,游客教育和游客满意仍然是四个主要运行目标之一。尽管国家公园管理局的每一级管理者都提供了塑造历史意义的背景,但是所有管理者都仍然恪守游客教育的首要目标。在多种层级的文化机构里工作的文化资源管理者和阐释者,能够揭示这些不同的背景和意义,也能揭示游客带来的不同背景和意义。
或者让我们想象一下,观众对诸如肯·伯恩斯(Ken Burns)的《美国内战》(The Civil War)这样的大众历史纪录片的反应喜马拉雅听历史版本。1991年3月间,我阅读了伯恩斯在其新罕布什尔的家中收到的信件历史解释怎么答,以此作为开始理解观众是如何构建他们所看到和听到的美国内战的意义的一种方式。许多来信者都讨论了他们是如何从家庭那里学到了关于美国内战的知识的。伯恩斯收到的信件中,约有三分之一提到了家庭成员,这表明,观众是透过他们的家庭史棱镜来看待这部影片所呈现的美国历史的。
历史不仅能用于传递意识形态和群体认同,或者用于牟利,而且还可以帮助个体在特定的环境中定位。历史意识和地域意识是不可避免地交织在一起的。我们把历史与地域联系在一起,而依附于一个地域的环境价值,在很大程度上源自记忆,以及我们所供职的历史研究学会。无论是放映一场关于内战战役的电影,对某个地方历史遗址或街区进行命名、保护和阐释,还是建立雕像或标志物,都会将过去事件的故事与特定的当前环境相联系。当某种环境被认为是“具有历史意义”的时候——无论是由政府指定的还是大众实践赋予的——会发生什么样的认知变化?当公民组织,譬如某个地方商会,创建地图和历史地图集确认某些历史地域而没有确认其他地域时,又会发生什么认知变化?对于文化资源管理者通过历史保护策略来帮助社区界定和保护他们的“特殊地域”和“特色”来说,关于记忆如何依附于地域的最新学术研究具有特殊意义。
在过去的10年里,正如历史学家已经研究了历史意识的形成——关于历史的观念是如何创建、制度化、传播、理解并随着时间变化的——一样,其他学科也考察了地域意识,环境心理学、民俗学和文化地理学的学者称之为“地域感知”(sense of place)。心理学家考察了儿童在成长的过程中,是如何将情感上的地域与儿童时代的地域记忆相联系起来的,他们尤其考察了6岁至12岁的儿童生活的环境,对成年人的个人认同来说,这个年龄段仍然是一个至关重要的节点。一个人的地域感知会被成年时代所参与的社会网络得到进一步发展和强化;一个人在某个地方生活的时间越长,那么对于与家庭和朋友的重要生活经历的记忆来说,环境的影响就越大。心理学家还研究了人与地域之间的这种纽带遭到破坏后的情感影响,当年长者丧失家园或流放者离开他们熟悉的环境和记忆地点时,他们就会感到极为痛苦。在研究20世纪50年代为了给城市改建项目让路而重新安置波士顿500名居民的案例中,马克·弗里德(MarcFried)就指出,甚至是搬迁了两年之后,仍有几乎一半居民患有抑郁症。波士顿的“西区”在记忆中获得了一种可能在经历上永远无法获得、但可以理解的地域——一些被破坏的街道,主要通过其被破坏的记忆,成为了唯一的“社区”或地域。
心理学家将地域感知与个人认同和回忆联系在一起,文化地理学家和民俗学家则将之与群体社会和集体记忆联系在一起。通过与家人和朋友交谈关于过去的地方性特征、关于天气、关于工作的经历,当地居民把普通的环境转变成了“有故事的场所”。华莱士·斯蒂格(Wallace Stegner)指出:“在某个地方发生的事情被铭记于历史、民歌、故事、传说或纪念物之前,任何地域都不成其为地域。”与力图捕捉和保存乡村地区土著人的浪漫“地域精神”的早期民俗研究不同的是,最新的研究集中关注的,通常是在同样的环境下社会群体之间交流的相互冲突的含义,以及“集体”地域感知的发明——就像公众史学的发明那样——是如何成为文化霸争的一部分的,这种霸权则是不同的群体和利益之间权力关系的产物。关注地域形成的意识形态方面内容的地理学家,力图对空间的社会生产进行批判性的分析,以此补充心理学研究和民俗研究对地域的主观经验分析。地理学家关注的是,地域感知是如何受到更大的社会、经济和力量的影响——比如说,这些力量决定了某个区域的贫民区和郊区的分布——以及谁获得了体验哪种地域的经历。某个地域的既有意义,以及因土地使用及规划决策而衍生的意义,不仅是某个城镇或社区不同居民之间沟通的结果,还是当地居民和外部世界沟通的结果。

关于地域感知的心理学、民俗学和地理学研究提醒我们,管理文化资源不 可避免地也是一种管理附着于某个地域的多重环境认知、价值观和意义的努力; 当某些地域被赋予具有“历史意义”并且区别于普通地域,或者当这些地域固 定化喜马拉雅听历史版本、被修复、抑或甚至重建时,那么哪一种(以及谁的)社区、地域和特征 会占据主导地位?在研究游客与历史遗址和文化资源的关系时,这是一个尤其 重要的问题。一般而言历史解释怎么答,游客在某个景观中寻找的是新奇感,也就是哪些东西 是与家乡不同的,而当地居民则把这个景观看作是记忆遗址和社会互动的网络。
对记忆和地域的研究应当是文化资源管理工作的一项常规内容。资源管理者可以发起一些活动,辨别和保护某个社区的记忆遗址、某些无意保存或由大众实践赋予特殊意义的地域,以及辨别和保护那些被政府赋予了重要集体认同的遗址,譬如曾经的战场和总统家乡,以及那些用来吸引游客的地方商会。1991年,我考察了“城镇性格”(town character)这个概念是如何在三个新英格兰社区使用的:诺斯菲尔德(Northfield),被印在明信片上的一个新英格兰村庄;威尔布拉汉(Wilbraham),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快速蔓延开来的一个郊区;以及斯普林菲尔德麦克奈特(McKnight)历史街区,一个种族多元化的都市街区。在一系列公众听证会中,居民们讨论了他们各自城镇或街区的“特殊地域”。历史遗址(暗指官方认可的)与社区记忆场所是不同的。比如,对于从贫民区搬进来的中产阶级非裔美国人居民和从郊区搬过来的中产阶级白人居民来说,重新修复的斯普林菲尔德麦克奈特历史街区的维多利亚式建筑具有不同的意义。
还有一些公众项目也能唤起社区的地域感知和历史感知,比如摄影项目、当地居民带领的社区徒步旅行,或者类似波士顿的“地铁上的艺术”那样的公共艺术项目,在该项目中,社区口述史学家与艺术家合作开发的公共艺术,在沿地铁橙线的每个站点都有配置。通过将全国背景加入当地居民的情感依恋之中,文化资源管理者有能力带给当地居民一些地域感。他们可以帮助居民和游客看到普通人看不到的东西:依附于地域的记忆和塑造了地域如何形成的更大的社会和经济进程。
关于记忆的最新学术研究有可能为文化资源管理者和学院派学者提供一个新的合作框架。关于记忆的新的研究路径,集中关注的是个人与群体是如何建立了他们对过去的理解的,可以用作以下三种历史活动的操作基础。史或官方历史、公众历史以及地域历史都使公众作为参与者加入到这些遗址所创造的历史之中。文化资源管理者和阐释者在这三种活动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希望本文所讨论的观点历史解释怎么答,即历史意义是如何被创造出来的,有助于文化资源管理专家和学院派学者准确、有效和全面地呈现过去。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免责声明:本站所有信息均搜集自互联网,并不代表本站观点,本站不对其真实合法性负责。如有信息侵犯了您的权益,请告知,本站将立刻处理。联系QQ:16407311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