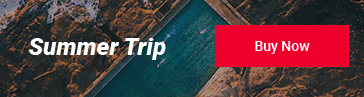历史专业名词解释动量概念的历史历史结论和历史解释历史题怎么概括特点
信息来源:互联网 发布时间:2023-05-29

例举式罪刑条款之所以成为口袋罪,是由于司法者未能遵循同类解释规则之所致。同类解释规则是发端于古罗马而适用于例示式法律规定的古老解释规则,其基本内涵为例举式条款中兜底项的解释事项只限于与列举项同类的事项。刑法同类解释规则只适用于以“等”、“其他”之类为省略标志的例举式罪刑条款,无此类省略标志的列举式罪刑条款不能适用该规则。基于公平原则、犯罪构成和法律解释的要求,适用同类解释规则解释例举式罪刑条款中兜底项具有必要性;而列举项具有相对明确的内涵和外延等特性,能够给兜底项提供解释参照、同类基准,使得同类解释规则适用于兜底项的解释具有可行性。从方便司法实践的角度来看,判断罪刑条款中兜底项与列举项是否属于同类,可以从“手段相似、性质相同、后果相当”这三个方面来把握同类标准历史题怎么概括特点。刑法同类解释的司法操作,包括确定判断基准、分析系争案型和比对两个案型等三个步骤。
在进入具体阐释本文论题之前,先来简要地谈谈口袋罪。所谓口袋罪,按照360百科的“指的是对某一行为是否触犯某一法条不明确,但与某一法条的相似,而直接适用该法条定罪的情况历史专业名词解释,这种情况多次出现,就将此罪戏称为口袋罪。”[1]而张明楷教授的说法是:“‘口袋罪’一词一般是在贬义上使用的,即各种各样并不一定符合该罪构成要件的行为,也被认定为该罪。”[2]套用坊间的一种形象说法便是:“口袋罪是个筐,啥行为都能往里装。”按此说法,口袋罪是指某一罪名的罪状过于宽泛或司法适用不当,以致许多不论是否构成犯罪的危害行为都能够在该罪名之下被定罪处罚。
众所周知,我国首部刑法即1979年刑法有三大口袋罪:投机倒把罪、流氓罪和玩忽职守罪。在那个年代尤其是“八三严打”时期,不知有多少不应该入罪的行为被“装”进这些口袋罪!曾经和刘晓庆、陈冲等同为中国国内影坛新星的迟志强,只因为随一些子弟看内部、与女伴跳贴面舞,[3]还有在轿车里女伴坐在了他的大腿上,就被以流氓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4]而被媒体称为“中国最后的一个流氓犯”的 牛玉强,却因两个并不起眼且事实不明朗的行为,[5]于1984年年仅18岁时被以流氓罪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其间由于保外就医而在重新收监后刑期被延至2020年。
现行刑法又出现两个新的口袋罪: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和非法经营罪。前者的典例有如:2001年10月18日,被告人肖永灵以食品干燥剂假冒炭疽杆菌装入两只信封内,并寄给上海市政府某领导和上海东方电视台某工作人员,造成拆信人精神上的高度紧张,同时引起周围人们的恐慌。法院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对肖判处有期徒刑4年。[6]后者则有新近的收购玉米典例: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市农民王力军,从临近村庄收购玉米贩卖给粮库或公司。因未办粮食经营许可证及工商执照,2016年4月15日被以非法经营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退缴的非法获利人民币六千元。[7]
那么之所以会出现口袋罪,究其原因大体上有两个方面:一是由立法上的规定过简之所致,主要体现在以抽象语词(简单罪状)概括犯罪构成的罪刑条款上。投机倒把罪、玩忽职守罪之所以成为口袋罪,主要原因就在于此。二是因司法上的解释偏差之所致,主要体现在未能遵循例举式罪刑条款的同类解释规则上。流氓罪、以其他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和非法经营罪之所以成为口袋罪,主要原因就为此列。[8]前述两种罪刑条款的主要区别在于:前者内涵外延不确定,需要通过价值补充来解释;后者至少列举项的内涵与外延是确定的,兜底项的内涵外延能够通过同类解释予以确定。本文仅对后者的同类解释规则予以具体阐释,并对一些观点加以商榷。
同类规则是发端于古罗马而适用于例示式法律规定的古老解释规则。古罗马时期已出现在证书、制定法中写上特定事项,并对有关同类内容予以省略的例示主义立法,[9]基此同类解释规则应运而生。在英美法系历史题怎么概括特点,则有“只含同类”的法律解释格言。英国德累杰尔官将同类规则概括为:“在列举的,但未被穷尽的可以被认为是某一种类的人或物之后发现有概括性用词时,对这些概括性用词的解释只能限于该种类的事物,除非该项法律的全文与总范围合理表明,议会意在赋予它们以更为广泛的含义。”[10]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判决中指出,在列举特定类别、特定人或事之后尚附有总括性语词者,则其只应与所列举之人、事有相同的性质或类型。[11]
在我国,较早介绍同类解释规则的是储槐植教授。他指出:“如果一项刑事法律在列举了几个情况之后跟随着一个总括词语,如‘以及诸如此类’,那就意味着只限于包括未列举的同类情况,而不包括不同类情况。”[12]之后,该规则被国内许多法学专家运用于涉及法律兜底条款的理解和适用讨论之中,在刑法上尤其被运用于对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非法经营罪兜底条款的理解和适用的论辩。[13]新近也有一些专家对该规则提出质疑,认为“只含同类规则虽然不否认补充功能,但难以兼顾各种情况,其判断标准也欠缺必要的确定性,因而并非解释该条款的统一法则。”[14]不过该质疑毕竟只属少数之声,而对同类解释规则持肯定立场的仍是主流。最高法院于2016年12月16日指令巴彦淖尔市中级法院再审王力军收购玉米案,实际上也运用了该规则。[15]
对于刑法解释的同类规则,不同的论者虽有各异的表述,但所表达的意思却大体一致。上述德累杰尔官、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判例和储教授的表述,已经比较完整地表述了该规则的内涵。这里再摘录两种较为详细的国内学者的说法:“只含同类规则,即当刑法语词含义不清时,对附随于确定性语词之后的总括性语词的含义,应当根据确定性语词所涉及的同类或者同级事项予以确定。”[16]“同类解释规则是指当刑法列举了相关事项的同时又设置了概括性规定时,对于附随于确定性词语之后的概括性词语,应当根据确定性词语所涉及的同类事项确定其含义及范围。即运用列举和概括两种方法来共同表述概念的,概括的方法所表述的概念的外延应与列举方法所表述的概念的外延处在同一个层级上历史题怎么概括特点。”[17]
理解刑法上同类解释规则的基本内涵,需要把握如下几个要点:首先,适用场合。同类解释是对例举式罪刑条款中的兜底项的解释规则,其适用场合限于例举式罪刑条款而不能扩及列举式罪行规定。其次,宽严取向。例举式罪刑条款的是堵截构成要件,其功能主要在于限制其适用范围,因而应该坚持严格解释而不能认为可以任意解释。其三,解释标准。应当以例举式罪刑条款中的列举项规定的法定案型作为同类解释的基础和参照,只有与其基本相当的系争案型才能够被解释到兜底项中去。其四,操作要求。解释者必须客观地寻求系争案型与法定案型的一致性或同类性。正如论者所言:“不仅要从各种实实在在的具体案件中抽象出作为案件处理标准的正义观,更重要的是要深入理解具体兜底条款的内在含义,从而使得其符合正义的要求,并最终体现法律的正义性。”[18]
刑法解释的同类规则适用于例举式罪刑条款,这在学界并无异议。然而,对于何谓例举式罪刑条款则有不同观点。通常认为例举式罪刑条款是在列举至少一个事项之后,以诸如“等”、“其他”之类的省略标志,对被省略的事项加以概括或兜底。例如,“在制定法中,例示规定包括以‘其他’与‘等’为标识的两类法条形式”;“在形式上,例示规定的标识词语是‘其他’与‘等’”。[19]然而有一种观点则认为,有省略标志的是典型模式(经常类型),而没有省略标志的是不典型模式(形态类型),两者都属于例举式规定。“本质上而言省略无需标志,标志只是一种常见现象而已,明示省略需要标志,而默示省略不需要标志。”[20]对此笔者不能苟同。暂且不论此种观点在非刑事法律规定上能否适用,不适用于刑法的例举式规定则应是确定无疑的。
刑法实行的是罪刑法定原则。《刑法》第三条规定:“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定罪处刑;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刑。”例举式罪刑条款的功能,在于将与已列举事项同类的“等”、“其他”事项纳入刑法调整,关乎“等”、“其他”行为是否应当入罪的大问题。按照罪刑法定原则,只有刑法规定中以“等”、“其他”为省略标志的,才需判断罪刑条款列举之外的行为是否入罪。而刑法规定虽有列举多个事项但无“等”、“其他”省略标志的,是列举式罪刑条款。立法上采用列举式罪刑条款,表明立法者只将列举的事项纳入刑法调整,所涉行为才予以入罪,而不允许法无明文而入罪。我国刑法早已废止了类推制度,不应当认为未以“等”、“其他”省略标志所概括的行为,与刑法规定已列举的事项“同类”而将其入罪。[21]
同类解释属于狭释,而不能是刑法罪刑条款所不允许的漏洞补充,[22]其首要方法是文面解释。而文面解释的第一要义,就是“一字不漏规则”。在这方面,许多法律巨匠都做了阐述。例如,贝卡利亚在其著名的《论犯罪与刑法》一书中写道:“当一部法典业已厘定,就应逐字遵守。”[23]1940年,美国最高法院首席法官罗杰泰.勒在谈到宪法解释时也说:“在解释中必须赋予美国宪法每一个字以应有效力和恰当含义……每一个细心酌斟的字都颇有份量,其效力和要旨都经周详考虑。因此,宪法文字无一多余或无用 ……”。[24]美国学者安修也指出:“对法律的字释要全面,每一个字、词、短句和句子均为有效,不应被忽略、遗漏、舍弃或闲置。”[25]
前述“不典型模式”之说,实则混同例举式规定与列举式规定。两者虽只有一字之差,却是有着本质区别的两种立法模式。前者是不完全列举,以“等”、“其他”之类省略标志作为兜底,表明该规定的调整对象不限于已列举的事项;后者则是完全列举,没有“等”(等外)、“其他”之类省略标志,表明该规定的调整对象仅限于已列举的事项。质言之,两种立法模式体现着相反的立法意图。因此,两者在解释上适用的规则也就南辕北辙:前者适用“同类解释”规则,后者则适用“明示其一即排除其他”规则。可见,将列举且无省略标志的刑法规定视为例举式规定的不典型模式或形态类型,进而适用同类解释规则扩大其调整范围的观点,起码在刑法解释上是不能接受的。
本部分从为何需要同类解释与何以能够同类解释两个角度,来阐释刑法兜底规定同类解释规则的法理依据。进行任何事务,均需考虑需要与可能。需要也即讲必要性,无必要性也就失去做出有意义行为的前提,因而即使做出也是毫无价值的。可能也即讲可行性,无可行性即使需要也不能实现行为的的目的,因而也是徒然的。对刑法兜底规定的同类解释规则适用而言,同样是这样的道理。如果没有必要以同类解释规则来解释刑法兜底规定,或者有其他更好或更简易的解释方法能够得出更确切的解释结果,那么同类解释规则对于刑法兜底规定也就没有适用的价值历史题怎么概括特点。而如果同类解释规则对于刑法兜底规定的解释没有可行性,即无法进行或者不能得出恰当的解释结果,那么即使需要以同类解释规则来解释刑法兜底规定也是徒然,必须另辟蹊径,寻找其他解释方法。
对于为何需要同类解释,理由主要有如下三个方面:其一,基于公平原则的要求:相同案件相同处理。反过来说,刑事上予以相同处罚的行为应当具有同等的危害程度。例举式罪刑条款中列举项规定的行为与未列举的兜底项行为适用同一个法定刑,因而只有对兜底项行为与列举项行为予以同类解释才符合公平原则。否则,将未达到同等危害程度的行为予以相同处罚,则属罚不当罪。其二,基于犯罪构成的要求:犯罪构成是认定犯罪的唯一法律标准。兜底项行为只有与列举项行为的犯罪构成相同,才能构成该罪刑规定的犯罪。否则,将未满足列举项行为的犯罪构成拔高适用该规定,则属非罪入刑。其三,基于法律解释的要求:使法律之间相协调是最好的解释方法。[26]只有将兜底项的和列举项的行为作同类解释,才能使法律之间相协调。这也是刑事一体化的题中之义:“‘刑事一体化’就是要求对兜底条款的解释要与这些法律规定的确定的犯罪行为要一致,统一,以便整个法条内涵的‘一体化’”。[27]
至于何以能够同类解释,原因在于例举式罪刑条款本身。例举式罪刑条款的完整结构为“:列举项+兜底项+情节项+定性项=法定刑”。其中:1、列举项至少为一个,通常是两个以上;2、兜底项以“等”、“其他”之类的省略词加以概括,是需要解释的对象;3、情节项、定性项和法定刑及于列举项和兜底项,系列举项和兜底项所共有。需要指出的是,情节项和定性项未必都存在于同一罪刑条款中,但一个罪刑条款必有其中的一项。[28]就同类解释规则的适用而言,具有直接意义的是列举项与兜底项。因为所谓同类,所指的就是兜底项与列举项应当同类。这种同类首先是兜底项与列举项的内涵、外延的同类,之后才是性质、情节(后果)上的同类。且对于没有情节项或定性项的罪刑法条,兜底项的情节或性质也须从列举项中去探寻。
那么,列举项之所以能够为兜底项的解释提供参照?这主要是因为兜底项本身没有实在的内涵历史结论和历史解释,自然也就不可能从其本身来确定外延。而相对于兜底项,列举项有着比较明确的内涵与外延。这种较为明确的列举项的内涵与外延,基于“同类”的要求也就限定了兜底项的内涵与外延。质疑同类解释规则的论者认为列举项本身的内涵与外延也须通过解释才能明确,依此否定同类解释规则的价值或可行性。[29]其实,列举项本身能够通过解释而使其内涵与外延明确,是因为列举项本身已经蕴含者其内涵和外延,解释只是将其揭示而已。但兜底项则不同,其本身并无蕴含着内涵和外延历史题怎么概括特点,因而需要以列举项为其解释的参照。用语用学的话来说,这是言内语境尤其是其中的句内语境所决定的。[30]因此,不能因为列举项本身需要解释而否认同类解释规则对兜底项解释的价值。
同类标准是同类解释规则最为核心的内容,也是最难解决的问题。对此,论者们相继提出了类似情形说、相当说、同一类型说、实质相同说、语词类同说、等价性说等观点。[31]类似情形说主张兜底项应与列举项的情形类似;[32]相当说则认为兜底项须与列举项的行为相当;[33]同一类型说提出应进行类型性判断动量概念的历史,即兜底项应与列举项属于同一类型;[34]实质相同说提出,兜底项应与列举项具有“同质性信息”;[35]持语词类同说者主张,兜底项与列举项之间体现属性方面的类同;[36]等价性说则主张,兜底项应与列举项具有“等价性”、“相当性”。[37]应该说,这些观点基本上可以认为是大同小异,都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同类解释之同类标准。而从方便司法实践的角度来看,判断罪刑条款中兜底项与列举项是否属于同类,可以从“手段相似、性质相同、后果相当”这三个方面来把握同类标准。
首先是手段相似。所谓兜底项的解释,实质上是对某个系争案型(现实案型或想象案型)是否可以纳入兜底项予以罪刑调整的判断。因而所谓同类解释,也就是对拟纳入兜底项调整的系争案型与列举项中的法定案型是否属于同一类型的比较。根据“由表及里”的认识规律,两种事物的异同需要从其表象开始比较。而犯罪手段是犯罪人实施具体犯罪的客观行为方式,是认识某种犯罪的第一表象。犯罪手段还是犯罪构成客观方面的重要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犯罪行为的性质。因而拟纳入兜底项调整的系争案型与列举项的法定案型是否同类,首先要从比较两者的行为手段入手。这种比较的关键,在于抓住并比较系争案型与法定案型的行为手段的基本特征。之后运用类比的逻辑推理,判断两种案型的行为手段是否具有相似性以及相似度的高低。具有相似性且相似度较高的,可以初步认为两者属于同类。
其次是性质相同。认识事物必须“透过现象看本质”,只有把握事物的本质才是真正认识了该事物。把握系争案型与法定案型行为手段上的相似性,只是初步判断两者为同类。而且刑法实行罪刑法定原则,类推适用已被禁止。前述行为手段相似的类比只是解释方法上的,而要将系争案型纳入兜底项调整已经跨入刑法适用范畴。所以同类解释规则中的同类,还须是性质上的相同。刑法原理告诉我们历史结论和历史解释,犯罪客体(侵犯法益)决定犯罪性质。因而系争案型与法定案型是否同类,主要是指两者的犯罪客体或称侵犯的法益是否相同。也就是说,只有系争案型与法定案型在手段上相似、性质上相同,才能确定两者属于同类,才有将系争案型纳入兜底项调整的可能。但是,如果系争案型已被其他罪刑条款规定为独立的犯罪,原则上不能纳入兜底项调整。这是“禁止向一般条款逃逸”法律适用原则的题中之义历史题怎么概括特点,除非例举式罪刑条款的法定型更高需要适用法条竞合从一重处断。
最后是后果相当。我国刑法的罪刑规定,采用的是“定性+定量”模式。基此,即使拟纳入兜底项调整的系争案型与列举项规定的法定案型在性质上相同,仍不能据此而将其纳入兜底项予以定罪量刑。只有系争案型与法定案型既为同质又在量上达到相当的程度也即后果相当,才可以最终将系争案型纳入兜底项予以罪刑调整。例如,王力军收购玉米贩卖给粮库或公司却未办粮食经营许可证及工商执照,依当时的相关规定确实属于非法经营。然而,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规定的非法经营罪在客观方面,必须是“扰乱市场秩序,情节严重”或“ 严重扰乱市场秩序”历史专业名词解释。王力军的非法经营行为并未达到“严重”的程度,因而原判根据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第四项规定以非法经营罪对王力军定罪判刑,自然也就是适用法律错误应该予以再审改判的了。从这里可以看出,后果相当应该是同类解释中判断同类的最终标准。基此,同类解释更为严格地说应该称为“相当解释”。
在刑法同类解释的司法操作方面,储槐植教授有段权威的阐述:“根据只含同类规则,司法者在适用解释刑法时,应当通过与法条在罪状中明确列举的构成要件要素的类比推断历史专业名词解释,明确界定总括性构成要件要素的内涵,从而满足刑法明确和确定的要求。为了避免解释的随意性,解释时应根据类比的对象而定,即‘或者其他’之前的情形是参照物,以其他基本相当的情形才可被解释到‘其他’这一用语的内涵之中。按照只含同类规则,这种总括性语词的含义只限于未被明确列举的性质、情状与具体列举的情形或事项类同或基本相当的其他情形或事项,而不包括不类同或不相当的其他情形或事项。”[38]储教授的这一阐述,为刑法同类解释的司法操作指明了基本方向、揭示了其主要原则。本文试从以下三个阶段,阐述刑法同类解释的具体步骤:
一是确定判断基准。即确定判断拟纳入兜底项调整的系争案型与列举项规定的法定案型是否属于同类(或相当)的标准,包括犯罪行为特征、行为性质和行为后果等三个方面的内容。根据例举式罪刑条款的规定要素,应当把握这样三个确定原则:其一,不论例举式罪刑条款是否规定情节项和定性项,行为特征均须从列举项规定的法定案型中提取或探寻;其二,例举式罪刑条款已经规定情节项或定性项的历史结论和历史解释,行为性质或行为后果根据情节项或定性项确定;其三,例举式罪刑条款规定的情节项或定性项抽象模糊的,应以列举项为参照确定行为性质或行为后果。质言之,除非例举式罪刑条款规定了具体明确的情节项和定性项,同类解释的同类判断基准需从列举项的法定案型中提取或探寻。需要指出的是,兜底条款不等于兜底项,它还可能包含情节项和定性项,[39]因而不能认为兜底项解释的参照物可以是兜底项本身。
二是分析系争案型。上已指出所谓解释兜底项,实质上是系争案型是否可以纳入兜底项予以罪刑调整。而按照同类解释规则,拟纳入兜底项的系争案型须与列举项规定的法定案型同类。这就需要对系争案型的行为特征、行为性质和行为后果进行分析概括,以便与法定案型或上述同类的判断基准加以比对。这里涉及同类解释规则的目的需要澄清。有论者认为,同类规则的目的是还原被省略的内容:“‘同类规则’就是将例示主义立法模式下省略的内容予以还原的一种解释规则”;“从根本上说同类规则不是用来解释概括词而是还原被省略内容”。[40]这种说法对于抽象式司法解释或有些许道理,但绝不适用于司法过程中裁判解释。即使是抽象式的司法解释,“还原被省略内容”即想象案型也应与列举项规定的法定案型同类才能还原,因而同样需要对系争案型进行分析。
三是比对两个案型。即将系争案型的分析结果与同类的判断基准,从行为特征、行为性质和行为后果等三个方面进行比对,确定系争案型是否与法定案型同类或相当。同类或相当者,纳入兜底项予以罪刑调整,否则不得纳入。系争案型与法定案型的行为特征比对,需要运用类比方法确定两者的手段是否相似。系争案型与法定案型的行为性质比对,须以例举式罪刑条款规定或从法定案型中探寻的行为性质为基准,而且两者须达到性质相同的程度而不仅仅是相似,这是罪刑法定和禁止类推原则的必然要求。而系争案型与法定案型的行为后果比对,则要求达到两者后果相当的程度。所谓相当也就是基本相同,这须用类型思维加以判断。两者的行为后果不达相当者,实际上就是系争案型不符合例举式罪刑条款规定的犯罪构成,因而不能将其纳入兜底项予以罪刑调整历史专业名词解释。而系争案型的行为后果比法定案型的更甚者动量概念的历史,则属适用当然推导的举轻而明重规则而非相同解释规则。
[2] 张明楷:《论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扩大适用的成因与限制适用的规则》,载《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12年第4期。
[3] 参见水颜水色:《爆演员迟志强为什么坐牢,迟志强简历及近况坐牢照片》动量概念的历史,原始网址: ,2017年7月10日访问。
[5] 两起事件的情形为:“翻开1984年4月28日由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刑事判决书》显示的牛玉强的犯罪事实,第一起是1983年5月的一天(原文没有具体时间),牛玉强和几个朋友在北京某地抢了一名路人的一顶帽子;第二起则是牛玉强和朋友与另外几个人打了一架,至于打架到底造成了对方什么样的伤害,当时的判决书上并没有法医伤害鉴定。”王晓易:《抢帽子牛玉强成中国最后的“流氓”》,载《华龙网-重庆商报》2010年12月6日,原始网址 ,2017年7月10日访问。
[6] 参见游伟、谢锡美:《论罪刑法定原则的价值及其实现——全国首例投寄虚假炭疽恐吓邮件案定性研究》,载《福建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2002年04期。
[7] 参见郭路瑶:《探访内蒙古无证收购玉米获刑农民:绊倒在贩粮路上》,载《千龙网-中国首都网》2017年1月11日,原始网址 ,2017年7月10日访问。
[8] 按照储槐植教授的提法,前者规定的是弹性构成要件,后者规定的为“或者其他”型堵截构成要件构成要件。储槐植:《刑事一体化与关系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58-359,361页。
[10] 转引自孔祥俊:《法律解释方法与判解研究》,人民法院出版社2004年版,第485页。
[13] 比如,张明楷教授运用同类解释规则,分析司法中对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认定所存在的九大问题,指出之所以出现司法上的误判,原因就在于没有遵循统一解释规则。详见张明楷:《论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扩大适用的成因与限制适用的规则”》,载《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12年第4期。
[15] 最高人民法院指出,刑法第225条第(四)项是在前三项规定明确列举的三类非法经营行为具体情形的基础上,规定的一个兜底性条款,在司法实践中适用该项规定应当特别慎重,相关行为需有法律、司法解释的明确规定,且要具备与前三项规定行为相当的社会危害性和刑事处罚必要性,严格避免将一般的行政违法行为当作刑事犯罪来处理。
[17] 2014年司法考试刑法学历年真题解析:《关于刑法用语的解释,下列哪一选项是正确的?》之答案D;载《中华考试网》 2015年4月20日,原始网址:,2017年7月10日访问。
[18] 刘沐阳:《论兜底条款的同类解释规则》,载《新财经(理论版)》2013 年第12期。
[20] 王建林、伍玉联:《“同类规则”在刑法解释中的理解与适用--一个基于类型理论的思考》,载万鄂湘主编:《建设公平正义社会与刑事法律适用问题研究——全国法院第24届学术讨论会获奖论文集(下册) 》,人民法院出版社2012年版,第995页。
[21] 若某种危害行为与列举式罪刑条款所列举的犯罪不仅“行为同类”而且“危害更甚”,适用该列举式罪刑条款追究其刑事责任,则是属于当然推导中举轻明重规则的适用,而不是适用同类解释规则。
[22] 有些论者将例举式规定的功能定位予漏洞填充方面,因而认为同类解释规则存在妨碍例举式罪刑条款的功能发挥。这也是认为没有省略标志的刑法规定即所谓“形态类型”、“不典型模式”,也可以适用同类规则进行解释的认识误区之所在。本文认为,刑事立法上采用例举式规定,其目的或功能在于“防漏”而非“补漏”。“补漏”之说有悖于罪刑法定原则,罪刑条款只能“防漏”而不能进行“补漏”。
[24] 转引自[美]詹姆斯·安修:《美国宪法解释与判例》,黎建飞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3页。
[25] 转引自胡玉鸿主编:《法律原理与技术》,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71页。
[27] 余志征:《从兜底条款看刑法解释》,载《正义网》2013年12月13日,网页:,2017年7月10日访问。
[28] 例如:刑法第一百一十五条:放火、决水、爆炸……(列举项)或者以其他危险方法(兜底项)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情节项)的,处……(法定刑);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一款则为:以暴力、胁迫(列举项)或者其他手段(兜底项)妇女(定性项)的,处……(法定刑)。而第二百二十五条非法经营罪规定的前三项是列举项历史结论和历史解释,第四项“其他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非法经营行为”这一兜底条款,除了兜底项还包括情节项和定性项。但实际上该情节项和定性项在第一项之前就已有规定,第四项只是重复该两项规定,所起的是强调的作用。因此,进行同类解释时不能将该两项混同于兜底项,而认为列举项的解释需要以兜底项为参照,或者说两者在同类解释中互为参照。
[30] 语境可以分为三类,即言内语境,言伴语境,言外语境。而“‘言内语境’分为句内语境、句际语境和语篇语境三类”。详见彭志平:《“言内语境”在汉语课堂教学中的设置与利用》,载《世界汉语教学》 2012年01期。
[34] 详见陈兴良:《口袋罪的法教义学分析:以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为例》,载《与法律》2013年第3期。
[35] 详见刘宪权:《操纵证券、期货市场罪“兜底条款”解释规则的建构与应用》,载《中外法学》2013年第6期。
[37] 详见付立庆:《论刑法用语的明确性与概括性——从刑事立法技术的角度切入》,载《法律科学》2013年第2期。
[39] 比如刑法第二表二十五条第四项兜底条款“其他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非法经营行为”,其中的兜底项只是“其他行为”,而“严重扰乱市场秩序”、“ 非法经营”则分别属于情节项和定性项。
[40] 王建林、伍玉联:《“同类规则”在刑法解释中的理解与适用--一个基于类型理论的思考》,载万鄂湘主编:《建设公平正义社会与刑事法律适用问题研究——全国法院第24届学术讨论会获奖论文集(下册) 》,人民法院出版社2012年版,第994、995页。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免责声明:本站所有信息均搜集自互联网,并不代表本站观点,本站不对其真实合法性负责。如有信息侵犯了您的权益,请告知,本站将立刻处理。联系QQ:1640731186
 5
5
 0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