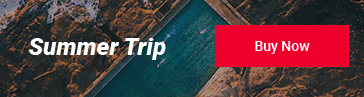历史新闻大事件历史大事年表高中cctv历史频道
信息来源:互联网 发布时间:2023-05-27

王金红最终还是没有顶住压力,张庄的地分了。而当年作为妥协,保留搞机械化试点的700亩土地,最后也因为村内人口增加陆续承包给个人了。“因为新增加人口的,就要调节一些。生个孩子,30年后才有地,怎么办?”王金红说。
2004年王金红退休了,不再担任。退休前,他曾去参观过南街村,说起来既羡慕又遗憾:“华西,南街,就是我们当时走的路。人家没分,我们分了。集体的力量和现在的有利条件结合,现在的经营方式,效果特别好。”
但对于再回集体化,他却又表示出自己的忧虑,“从农业上替下来的劳力没有出路,机械化就不能成功。”张庄全村2000多亩土地,3000口人,一半是劳力。“上学一年能走几个?去外边打工,没有技术,没有门路,到长治打工,挣个六七八百,一算下来剩不下几个。”
“现在的问题是,即便出去打工,也是没有保障,所以对大多数农民来说既不能出去打工,也不敢丢地。”
除了劳力出路,还让王金红担心是利益保护的问题,这在王金红口中是“管理”的问题,而这无论对于集体,还是对于个人都是个难题。
他举了个例子。“水利局租了我们村200亩地,种土豆。成熟的时候,白天有人挖,晚上也有人挖。东西保不住。”
但在美国,这就绝对不存在。从1987年到2004年,王金红去了六次美国。就住在韩丁那2000亩的农场里,“那是他私人的。谁敢来?不管是政府,还是其他人,我不同意,谁敢来?”而在中国,“我有1000亩地,你没有地,会出问题!会嫉妒,会眼红。”
2008年10月13日上午,山西省长治市壶关县龙泉镇寨上村村民宋书平一家正在自家院子里收拾、晾晒刚从地里收回来的玉米。
2008年10月12日,十七届三中全会闭幕,通过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图为2008年7月,河北,一处农田里的农业机械在进行农业生产。
他们以世界强国的傲然姿态,去到那想象中水深火热的西方世界,却只能得到震惊与自惭。历史总是惊人相似,中国人又一次知耻而后勇,起自1978年官员出国潮。
“闭关自守,总以为自己是世界强国,动不动就支援第三世界,总认为资本主义腐朽没落,可走出国门一看,完全不是那么回事,你中国属于世界落后的那三分之二!”原广东省副省长王全国说,“那一个多月的考察,让我们大开眼界,思想豁然开朗,所见所闻震撼每一个人的心,可以说我们很受刺激!”
从1977年秋国家计委提出“8年引进65亿美元”,跳到“8年引资180-200亿美元”的新计划,只用了半年。手头储备的项目不足,国家计委就给中央打了个报告,“让干部出去看看,落实引进规划”,这就重启了出国考察之门。
与世隔绝20年,除了少数搞外交和外贸的干部外,大多数领导干部都没出过国。许多人,都是在1978年第一次出国,第一次身临其境地观察“腐朽的西方资本主义”历史新闻大事件。
宝钢离休干部张衍,就是跟着上海宝钢初步设计审查团到日本谈判去的。当时国家只发100元置装费,而他们每人要带两套外衣,只好借一套西装做一套中山装——毕竟,国内平时不穿西装,还是做中山装划算。
也有的单位统一订制了西装,当时有个广为流传的笑话:美国政府请中国代表团听音乐会,演出结束后,中国人涌向衣帽间,随便拿起一件就走,看得美国服务员目瞪口呆。原来,西装都是统一做的,从颜色款式上无从分辨,只好谁合适就给谁穿了。
翻开老照片,当年走出国门的干部,往往是身着笔挺西装,腕戴公家发的手表,手持标有编号的照相机,虽然兜里只有20元外汇券做零用钱,却显得并不寒酸。
当年对外部世界的热度,从中国社科院办的一份刊物——《经济研究参考资料》上,也能窥见一斑。这份刊物从1979年创刊到当年年底,已出了200期,其中刊登了出国考察报告的就有101期。在这101期中,又以出访日本、南斯拉夫、匈牙利、美国、西欧的见闻五分天下。
干部出访之集中,甚至给国外造成了压力。1980年有个统计,第四、五、六机械工业部与海军先后都派人到西德的同一家电池厂去考察,而日本名古屋市某厂则接待中国考察团达92个批次之多。
中国农业代表团在美国待了40天,就参观了102个单位,包括农庄、养猪场、渔港、农业大专院校、研究所等,皆有名有姓,有见闻有观感。以这种一天赶3个场子的频率算来,他们是无暇参观“赌城”拉斯维加斯了。
被派到西欧的农业专家就更敬业了,虽然他们不理解欧洲人为什么要养瘦肉猪,却暗地里抓了把饲料,打听着养瘦肉猪的技术,甚至还数出荷兰生猪比中国生猪多了两条肋骨,作为技术指标。
各路“侦察兵”中,最核心的,是由中央直接派出的“正规军”。此时,纳入中央考察视野的,有美、日及西欧的发达国家,还有苏联和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以及港澳地区。
以林乎加为团长的中国赴日经济代表团,考察战后日本的经验;以李一氓为团长,于光远、为副团长的中央代表团走访南斯拉夫;以段云为组长的港澳经济贸易考察团,对香港、澳门进行实地调研;副总理谷牧则带着经济团访问了法国、瑞士、比利时、丹麦、德国等西欧五国。
从代表团的名称看,考察方向显而易见,它们都冠以经贸之名。1977年9月在谈到学习外国时,主要提出两条:一是学习科学技术;二是学习科学管理——这是我们借鉴外国经验的大方向。
西方国家中,最先走入视野的是邻国日本。国家经委的考察团向汇报:在中国“”以前,日本经济和中国差不多,后来差距拉大,主要是我们在管理、技术上落后了。于是,当年就成立了质量管理协会,次年又成立了中国企业管理学会,举办管理干部研究班。
在东欧国家中,最先去探查的是南斯拉夫。南斯拉夫早在1950年代,就摒弃了从苏联引入的计划经济模式,试行市场经济。过去我们一直批判它是修正主义,访南后,才又承认它是社会主义国家了。
中央代表团访南后,对南斯拉夫的农工商联合企业印象深刻,就在国内也搞起了“贝科倍”(农工商联合体),在全国26个省、区的36个农垦单位试点,着实热闹了一番。
去香港的人回来以后,则在报告中第一次提出在宝安、珠海建设经济特区。6月3日,中央、国务院的主要听取汇报,原则上同意他们的提议,并要求“说干就干,把它办起来”,经济特区肇始于此。
西欧五国考察团团员、原国家计委副主任的杨波就总结说,改革开放其实是主要从香港拿到了资本cctv历史频道,从西方拿到了科技,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则有对东欧的借鉴。
在1978年出国潮中,最重要的一次出访,当属西欧五国之行。这是新中国首次向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派出国家级代表团,这也是直接推动了改革开放的一次访问。
代表团成员除了分管经济工作的副总理谷牧外,还有七八位部级干部和20余名长期从事经济工作的中央和地方领导。
从1978年5月2日到6月6日,代表团先后访问了5国的25个城市,参观了80多个工厂、矿山、港口、农场、大学和科研单位。行程之紧,可谓“坐着飞机看花”。
为了有备而去,出发前,考察团集中在北京做了一个多月的功课,不过这并不能避免“对牛弹琴”的第一次会见。
访问的第一站是法国。与法国总理雷蒙巴尔会谈时,谷牧团长按照国内准备的稿子,讲了外交,但没谈经济。单从表情看,就知道人家兴趣不大。后来,巴尔总理干脆直说,“问题我不谈,我就谈经济,问题我们总统跟你谈。”
在和法国总统德斯坦会谈时,总统又说,问题我们中间没什么好说的,还是谈谈经济吧。法国驻华大使则当着他们总统的面对谷牧说,听说你们要搞120个大项目,我们法国很愿意对中国有所贡献,给我们10个行不行?
为中国做贡献,可信吗?让考察团惊讶的是,他们还没回来,法国巴黎银行董事长已经先一步到京了,一来就提出了25亿美元的计划。
在西德,德国人对于“贡献”更是急切。北威州州长屈恩在欢迎宴会上说,“50亿美元,现在就签,200亿,宴会后谈判一小时签字。”
即便遇上这等好事,中国人阶级斗争那根弦可没放松,会谈中还批判人家搞绥靖政策,借钱给“苏修”,把“苏修”给喂肥了。德国的州长则诉苦说,资本也要找出路呀。
德国人知道中国对主权非常敏感,就出主意说,为了在不影响你们主权的情况下用我的资金,你们可以在欧洲开个银行,我们把钱存在你们的银行里,这是正常的信贷关系,不影响主权。
代表团也悟出了弦外之音:德国正在经历经济危机,资本过剩,开工不足,千亿游资都盯着中国这个巨大的市场。因为想和中国拉上关系的企业太多,代表团坐汽车已经参观不过来了,只好搭上军用直升机,一上午就走访三个厂子。
“现代化什么样?出去一看,噢,原来是这样!”在西欧五国考察团中,即使是1950年代出过国的,都没想到“腐朽的帝国主义”会发展得如此神速。
西德一个年产5000万吨褐煤的露天煤矿只用2000工人,而中国生产相同数量的煤需要16万工人,相差80倍。
瑞士伯尔尼公司一个低水头水力发电站,装机容量2.5万千瓦,职工只有12人。中国江西省江口水电站,当时装机2.6万千瓦,职工却有298人,高出20多倍。
法国马赛索尔梅尔钢厂年产350万吨钢只需7000工人,而中国武钢年产钢230万吨,却需要67000工人,相差14.5倍。
戴高乐机场,一分钟起落一架飞机,一小时60架;而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半小时起落一架,一小时起落两架,还搞得手忙脚乱。
访问日本的人回来介绍:日本普通工人家庭一般有四、五十平方米的住宅,全国平均每两户有一辆汽车,95%以上的人家有电视机、电冰箱、洗衣机,连农民都穿毛料子。日本东京的大型商店的商品多达50万种。
而我们呢,王府井百货大楼仅有商品2.2万种,城市职工20多年没涨工资历史新闻大事件,人均住房面积3.6平方米,拥有自行车、手表、缝纫机还是大多数家庭的追求,农村仍有2亿人没解决温饱,“实在觉得很寒碜”。
差距感是自然的,连都说:“最近我们的同志出去看了一下,越看越感到我们落后”。社会上甚至流传一种说法,“帝国主义是腐而不朽”。
一是从许多国家和地区的经验看,现代化是可以在短期内实现的。像日本、西德、丹麦以及东亚“四小龙”都只用了15年到20年的时间就富起来了。
二是我们的改革不愁没钱花。1974年石油危机后,资本主义正处于萧条时期,产品、技术、资本过剩,“急于找出路”,争相要和中国做买卖。
1978年6月30日下午,中央局听取了西欧五国行的考察汇报。这场汇报从下午3时半开始一直开到晚上11时15分,将近8个小时。
谷牧向中央领导讲了让他印象深刻的一件小事:在丹麦,农场主不能把农场随便转给儿子经营,儿子要想继承父业,必须从农业技术学校毕业,取得国家证书cctv历史频道,并且在其他农场实习两年才行。
主持汇报会的要求:考察人员继续深入讨论,研究出几条有情况分析、有行动措施的意见,提到国务院务务虚,进一步统一认识。
这次汇报后,又专门找谷牧去谈话。指示:引进这件事要做,重要的是争取时间。要缩短从谈判到进口的时间,一个项目能缩短半年,就是很大的利益。需要借点钱,出点利息,这不要紧,早投产一年半载,就都赚回来了,但质量要选好,要先进的。
由此看来,谷牧副总理兼任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的主任、国家外国投资管理委员会的主任,一直分管特区工作,都不是偶然。
从清末的洋务运动,到建国初期的向苏联老大哥学习,中国人开眼看世界的过程,时断时续,出现了一次又一次急转弯,每一轮学习往往意味着对上一轮所学知识的否定。
1978年的考察报告,围绕经济和技术打转。那么作为上层建筑的人的思想呢?较少见诸文字的,是大寨在1978年夏天那场思想大震动。
这年夏天,昔阳县委第一李喜慎,和大寨党支部郭凤莲参加中国农业考察团去美国考察了一个月。
他们回来向县里干部做了报告,美国种种,样样闻所未闻,见所未见。李喜慎聊起美国见闻来就说:“美国这个国家真怪,州长做报告,下面人可以乱提意见。州长的老婆也不安排一个好一点的工作。”
在过去的宣传中,我们把资本主义和失业、饥饿、挨冻、工厂倒闭、抢劫、、环境污染等直接连在一起,什么不好,什么就是资本主义的,就是不提人家的生产力、科学的发展。现在有人去世界上经济、科学最发达的美国看了一个月,眼见和过去听的宣传对不上号,而且反差如此之大,心理就承受不住了。
这个过去以批判资本主义而闻名世界的地方,思想乱了,一系列观念正在动摇。这还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的事。
不过,也有不为所动的人。郭凤莲也向大寨领头人陈永贵做了详细汇报,讲到美国农业的大机械化,讲到只有3.5%的劳力从事农业生产,讲到大豆(资讯行情)带、小麦(资讯行情)带cctv历史频道,相当于中国几个省的面积一色地种小麦或棉花。陈永贵细细听了,叹道:“好是好,咱没这个水平呀。就当是开开眼吧,资本主义这农业不简单哩!咱没人家那条件,咱们搞点小型机械……”
据当年的国务院港澳办公室统计,仅从1978年1月至11月底,经香港出国和去港考察的人员就达529批,共3213人,其中专程去港考察的有112批,共824人。
1978年的官员出国考察,比一百年前的清末“五大臣出洋”,来得规模大得多,给中国带来的直接影响,也更迅猛广泛。这一次,中国的门一旦打开,就关不上了。
即使在改革开放推进7年之后,中国人仍然发现前路层峦叠障、迷雾重重。而在长江急流险滩的那艘船上,通往市场经济的航道在瞭望者的眼中渐渐清晰起来。
1985年9月2日清晨6点,一声汽笛长鸣,“巴山”号游轮缓缓驶出重庆朝天门码头,朝着长江三峡的方向驶去。航程目的地是武汉,行程6天。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的赵人伟正在船上。这是一艘当年3月份刚刚下水的崭新轮船,额定载客80人,以2人标准间为主,配套有会议、休闲及健身功能,相当于三星级的宾馆,“在房间里就能洗澡呢,当时算很豪华了”,赵人伟至今记得。历时6天的 “宏观经济管理国际研讨会”就在船上召开,后人通常把这次会议称为“巴山轮会议”。
经济学圈内的人们早就听说了这次会的消息。许多人想方设法去上船听会。因为这次会议请来的中外嘉宾都非同小可。
外国人,有美国耶鲁大学经济学教授、1981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詹姆斯托宾,那句“不要把所有鸡蛋放到一个篮子里”名言的讲述者;英国剑桥大学教授、格拉斯哥大学名誉校长阿来克凯思克劳斯;英国牛津大学安瑟尼学院高级研究员弗拉基米尔布鲁斯;联邦德国证券抵押银行理事长奥特玛埃明格尔;匈牙利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部主任诺什科尔奈;南斯拉夫政府经济改革执行委员会委员亚历山大巴伊特;日本兴业银行(601166股吧)董事、调查部部长小林实等。堪称是一群当时世界一流的经济学家。
还有一位重要的外国代表,菲律宾籍华人林重庚。他当时是世界银行驻中国首席代表。巴山轮会议,最早是林重庚和中国体改委委员廖季立开始协商筹办的,廖季立后来因病未能与会。而参加会议的外国经济学家,主要也是林重庚请的。巴山轮会议以三家单位的名义主办: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中国社科院、世界银行驻京办事处。
中国方面,领衔者为年已81岁的经济学界元老薛暮桥,薛不仅是学界泰斗,而且曾任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等要职,当时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名誉主任;安志文,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兼党组;马洪,国务院经济技术社会发展研究中心总干事;童大林,体改委副主任,等等。这些都是参与制定国家经济政策的重要官员,年龄都在60岁上下。
除了官员,另一部分人是经济学家:刘国光(社科院副院长)、高尚全(体改委副主任)、吴敬琏(国务院发展中心)、赵人伟、张卓元(社科院财贸研究所所长)、周叔莲(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等。“可以说,当时社科院与经济有关的研究所所长,人都来了。”赵人伟回忆。除了刘国光外,这批学者多数当时50岁上下,正值壮年。
另有一批参加会议的“小字辈”,他们在今天格外引人注目:,46岁,时任财政部综合计划司副司长,后任财政部长,现刚从社保基金会理事长位置上退休不久;洪虎,45岁,时任体改委秘书长,现职全国人律委员会副主任;楼继伟,35岁,时任国办研究室主任,现职国务院副秘书长;郭树清,29岁,当时还是社科院博士研究生,现职建设银行(601939股吧)董事长。他和楼继伟,都是“挤”进来参加的会。
“当时年轻人还没起来。而我们这批人,包括来自体改委和社科院的这两部分学者,都是1978年以后投入改革开放中的,正站在改革的前沿。”对于这批后来成为中国改革中坚的学者们,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学理论显然已经不能解释现实问题,那么应该到哪里去寻求方向?——这不仅是学者们巨大的困惑,对于整个国家都是如此。
1985年,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进行到第7个年头。“从1979到80年代初那几年,中国刚改革开放,从计划经济一下跳到市场经济里,要一个过程。从高层决策者到经济学界,知识背景都不够。当时学习东欧的经验较多。无非是在原有的计划经济框架里,加点市场机制到里面。这方面东欧做得最多。但是东欧并没有把市场经济作为资源配置的基础,到了1985年,中国人觉得光学东欧改革是不够的了,也要学习西方的市场经济国家经验。1985年,是学习外国先进经验的一个转折点。”赵人伟这样评述巴山轮会议的背景。
1982年,十二大的报告,提出的还是“计划经济为主体,市场调节为补充”,到了1984年10月十二大三中全会,《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的说法已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赵人伟解释说:“商品经济就是市场经济,但是当时中国的官方文件中还没直接用市场经济这个词。从这个时候起历史大事年表高中,整个经济的轨道转到市场经济上了。没这个背景,巴山轮的会没法开。”
科尔奈,当时以一本《短缺经济学》赫赫有名。这位曾任匈牙利科学院计划中心部主任的教授,对计划经济的分析批判鞭辟入里。1982年,正在英国做访问学者的赵人伟读到《短缺经济学》的英文版,他的感觉是“震撼性的”。“我们对计划经济下的对传统的‘短缺’二字体会非常深。那时真是什么都缺,都要凭票,那是几代人经历过来的现实。在苏联,就表现为排长队。‘外部短缺和内部剩余’,‘投资饥饿’,这些都是过去经济学课本中从没听说过的。1985年科尔奈到我们所做报告,会议室里年轻人挤得水泄不通。”
到今天,科尔奈的祖国早已实行了市场经济。他后来的著作,在中国再没有当初那么大的影响,但在1985年,对于正向往摆脱计划经济的年轻一代中国人,他的声望如日中天。
科尔奈提出经济体制的四个模式,这四个模式又归为两大系统:行政协调;市场协调。郭树清后来在一篇综述中有很清楚的描述:行政协调,就是用行政手段管理经济,包括直接行政调控和间接行政调控(它们被称为1A和1B)。市场协调,决策是非集中化的,包括没有宏观调控的市场协调和有宏观调控的市场协调(它们被称为2A和2B)。
显然,中国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属于1A,即直接的行政协调,企业的供产销都由国家管。“这是我们要放弃的。改革的起点就从这里开始。但是2A,即没有宏观控制的市场协调,这种东西,今天世界上实际也没有。自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经济危机以来,2A在理论已经很难站得住脚了。剩下就是1B和2B。科尔奈提出,中国的经济改革目标应该是有宏观管理的市场协调即2B,而间接的行政协调即1B,只能作为一个过渡的模式。不要停留在这个模式上。”赵人伟说。
改革的目标,这是巴山轮会议讨论的首要议题。事后有人回忆,巴山轮会议的前三天,是“各说各话”。赵人伟说,经济学家们来自各国,学派也不同,当然各说各的。但是,在改革的目标上,代表们无论中外,基本一致:那就是肯定要改,而且目标是有宏观管理的市场协调模式。
巴山轮会议后,到1987年,十三大提出的是“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到了1992年南巡讲话以后,十四大正式确立定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
“巴山轮会议,对中央负责起草文件的人是有很大影响的。它既有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的背景,又对1992年确定市场经济有推动作用。它的最大的意义就在这里。”赵人伟总结道。
赵人伟回忆说,80年初,东欧的改革派经济学家到中国讲学,都是主张激进改革的。美国哈佛大学的赛克斯(Sacks)教授到苏联,讲的也是“休克疗法”。英国的布鲁斯教授,讲的也是“一揽子改革”,即改革不能单项突进,配套改革要一起上。但他们到中国后,都认为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只能搞渐进,不能搞激进。“中国经济发展太落后。地区差别很大。在德国或东欧国家,城乡差别基本没有了,工业化程度比较高。这样的社会搞激进都还有问题。另外根据1978年到1985年,六七年的改革经验来看,也不可能一蹴而就。先农村后城市,先沿海后内地,这样逐步推进的形势已经成型,一下子都改,做不到。”
这样,中国人就发明出了双轨制。“改革先从非国有的中小企业开始做,国有企业改革慢一点,先留在计划里面。但国企在整个经济中比重会越来越小。后来中国人熟悉的就是所谓‘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国有企业的存量,先不去动它,增加的发展的部分,进入新体制,按市场规律进行,这样减少震动。就是所谓的双轨制。”
“双轨制是谁发明的?争这个没多大意思,这是国外国内经济学界共同讨论的一个结果。1979到1980年,布鲁斯在讲课时就谈到这个问题了。1982年和1984年的莫干山会议都讨论过。这是一个集体智慧碰撞的结果。”赵人伟说。
按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张军的看法,在巴山轮会议上国外专家对于双轨制还是肯定的。双轨制并不是什么新提法,而中国人的新创造在于不仅生活资料双轨制历史大事年表高中,生产资料也搞双轨制。
但是双轨制必然有它的代价。“它会造成摩擦,”赵人伟说,布鲁斯讲过一个玩笑,说波兰人到英国学习交通管理。看到英国是实行车辆左行,回到波兰后,又不能全部改成车辆左行,就说,干脆一部分车右行历史新闻大事件,一部分车左行吧!布鲁斯的意思是说,你要学新的体制,就要彻底地改,不能改一半。中国的价格双轨制,必然产生寻租活动。这是渐进改革的代价。“所以后来外国经济学家们说,同意你们渐进改革,也同意双轨制,但时间不能太长。时间长了国家必然混乱——可是到今天,我们双轨制的问题还没有解决。”赵人伟说。
1985年的中国,正在经历经济过热带来的通货膨胀。这种经济过热,可以从下面一系列数字看出:1985年1月,工业生产增幅达25.2%,全年全民所有制固定资产投资增长24.5%,工资性现金支出增长27.3%。
吴敬琏在他的《当代中国经济改革》一书中提到这段历史时,讲到当时扩大专业银行自主权办法时的一项技术性错误:规定中央银行给予各银行的额度以1984年的实际发生额为基数。也就是说,1984年各银行贷出的钱越多,1985年他们能得到的额度就越高。
结果,各银行为了造这个基数不择手段,不但企业有求必应,甚至会送款上门,要求企业。而且,当时还有一项规定,企业使用工资奖金自主权时,也是以1984年的工资奖金总额为基数,导致各企业1984年年底突击提工资、发奖金。再加上1984年农业大丰收,银行没有留足收购款,中央银行不得不增发货币,终于使1984年的货币发行量比上年增长49.5%,多发了几乎一半。
“我查过当时的银行记录,银行的许多是流动资金的。”张军说,这说明历史大事年表高中,实际是银行把钱贷给企业,企业把钱作为工资奖金发掉了。货币发多了,必然造成物价上涨。尽管1984年零售物价指数只增长了2.8%,但1985年增长了8.8%。
此前在1980年代初,中国人已经历过一次物价上涨。但是张军说,那一次物价上涨,其实就是因为在价格上放开了一点,允许粮食、煤炭、石油超产的部分“以市场价格”在市场上卖。某种意义上,这还是一种相对价格调整。尽管也表现为价格有上升,但不等于是通货膨胀。而1984到1985年这次,是典型的通货膨胀,是货币发多了。
这是习惯了计划经济的中国人没有经历过的。计划经济下,物资虽然短缺,但物价不会上涨。现在搞市场经济了,通货膨胀也来了。该怎么办?
这时中国人发现,即使学东欧的改革,也未必能有好办法,因为当时的东欧也还不是真正的市场经济。不如直接去请教西方的经济学家,因为他们对发达的市场经济有丰富的宏观调控经验。
从英国来的凯恩克劳斯,对英国从战时经济体制转为战后经济体制很有研究,而且他实际操作过。“战时经济体制和计划经济很像。实物配置资源,价格不起作用。”赵人伟解释说。而当过德国中央银行行长的埃明格尔,主要是介绍在德国怎样通过货币政策进行宏观调控的经验。
巴山轮会议上,托宾对中国经济的宏观调控有个说法:像中国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用货币总量作为总需求管理不太可能。因为它的实际经济增长速度和货币流通量不确定,也没有西方那种得以影响货币总量的金融市场。相反,在中国直接控制利率和信贷更重要、更可行。
实际上中国对于经济过热的控制,从那时起到现在,大致也是用的直接控制利率和信贷这样的手段。“除了控制利率,还有控制货币供应量。每次调控都是管银行,把银行信贷的口子给关掉。其实还是比较行政的手段。”张军说。
在会上,外国专家们介绍说,西方国家中央银行控制货币供应总量的的方法不外三条:规定商业银行要在中央银行存入存款准备金;调整再贴现率;在“公开市场”买卖有价证券。
这里就谈到了中央银行的作用。在计划经济体制时期,中国只有中国人民银行,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中央银行。直到1983年9月国务院决定,中国人民银行专门行使中央银行职能。但是,张军说,那时中国人对于中央银行应是什么性质的机构,怎样管理宏观经济,也不是很清楚。所以有人说,中国人开始学习宏观经济调控,是从巴山轮开始。而且“宏观调控”这个词,也是从巴山轮会议出来的。张军介绍,当时英文的原文是“宏观管理”,当时大家有不同看法,有人认为应该宏观控制,有人认为应是宏观调整,后来就造出“宏观调控”这个词。
托宾告诉中国人,弥补财政赤字有两种方法,一种是增发货币,另一种是增加债券或税收。许多不发达国家特别是拉丁美洲国家长期遭受通货膨胀的原因,是它们只依靠增发货币来弥补赤字。相反,在实行了有效的宏观经济管理的国家,财政赤字很大,通货膨胀却并不严重,其原因就在于它们有一个完善的国内债券市场。
赵人伟回忆说,建立一个银行体系外的资金市场,这个议题在巴山轮会议上已经被提出来了,虽然只说到了债券市场,没有说到。“当时我们叫资金市场,不敢用资本市场这个词,似乎‘资本’就代表着剥削。但实际它们在英文里是一个词。”他笑道。
在巴山轮会议之后,对中国经济的宏观调控应该如何进行,适量的通货膨胀是不是有利于中国经济,始终是中国经济学家们争论的热点。1988年,中国又经历过一次更大规模的通货膨胀,引起全国空前的抢购风潮,人们不仅抢购电视机,连食盐、火柴都抢。通货膨胀与经济繁荣,似乎是中国经济的两极,每次经济过热了,就实行从紧的经济调控政策,于是经济发展就陷入低潮,慢慢积累着下一个。就这样,中国人在这两端的取舍中,学习着经济的宏观调控。
实际巴山轮会议也不光是中国人学习外国。张军还谈到,在1985年,大多数经济学家对中国的非国有部门的扩张和劳动力流动的发展速度显然大大低估了。实际上,中国的工资增长过快和消费膨胀的问题最终是在非国有部门的崛起与劳动力自由化的过程中最终解决掉的。而这些问题在当时的“巴山轮会议”上似乎还没有人能预料到。
“西方经济学家对发达的市场经济有丰富的宏观调控经验,另外他们有战时经济转型到和平经济的经验”,赵人伟说。“而中国给他们提供了从计划经济转型到市场经济的经验,这种转型中的调控,比正常的市场经济还要难。抛弃计划指令的同时,国家宏观调控没有跟上,往往会出现真空。我们的中国经验,是跟世界共享的。”
2006年3月4日在北京西山杏林山庄,由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高尚全组织的一次闭门会议,正式名称为“中国宏观经济与改革走势座谈会”,参会者有贺卫方、张维迎、杨东平、石小敏等人。会议分两个单元,第一个单元是就宏观改革形势进行讨论;第二单元是做“农民土地与农民工社会保障问题”。会议的主题是为了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针对近一、两年来社会上有关改革的大讨论,通过实事求是地分析,澄清认识,坚定方向,以期形成改革的共识与合力,提出措施建议,加快推进改革。
围绕当前关于改革的这场争论,大多数与会者认为,那些质疑改革开放的观点,特别是基于意识形态对改革的指责,基本上是没有说服力的。因为实践已经证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带给人们的只是经济发展的低效益与人民生活的贫穷与落后,改革的巨大成就是有目共睹的。但是,我们也必须直面改革过程中出现的一些具体问题,实事求是地分析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在此基础上才能形成改革的共识。
围绕当前广大群众关注的焦点问题,诸如医疗、教育、征地、收入分配差距扩大和政府官员等,大多数与会者认为,与其说是改革的不成功,不如说是一些领域中的改革起步晚了,进展慢了,改革的力度小了,使得长期形成的一些问题至今没有得到有效解决。因此,不能把当前出现的问题笼统地归结为市场化改革的失败。
就如何解决当前的一些深层次问题,与会者认为,解决收入分配不公,重点应调整积累与消费或者投资与消费的比例关系,应压缩基本建设投资规模,扩大政府对困难群体扶助的转移支付。针对医疗和教育领域中存在的问题,重点是破除垄断,政府应管好基础医疗与公共教育,同时放出一部分资源交由民间主体去创办;通过竞争,降低成本、提高服务质量,使老百姓得到实惠。在抑制的问题上,必须继续深化经济改革,特别是加快要素市场化的改革进程,破除行政性垄断,从制度上根除权力寻租的机会;同时,下决心加快推进体制改革,逐步建立起一套合理的行政管理体制与完善的法律制度。
1980年代中期,全国各地涌现出了一大批改革人物,如步鑫生、马胜利、禹作敏等,改革力量如日中天。1984年5月,在安徽合肥,由民间发起组织了一个 “世界新技术浪潮和中国改革研讨会”,是组织者之一。他们邀请了改革的先锋人物——凤阳县县委翁永曦、浙江海盐衬衫总厂厂长步鑫生、鞍山无缝钢管厂厂长王泽普,意在把全国的改革者联合起来,推动社会进步,甚至有进一步推动其他体制改革的意图。这个会以一个响亮的名字流传,叫“全国改革者大会”。
1984年9月初,由《经济日报》等媒体组织的“全国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学术讨论会”召开,因会议地址在杭州莫干山,也被称作是“莫干山会议”。此次会议的宗旨是 “为党和国家献计献策”,中心议题是城市经济体制改革。
莫干山会议在改革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被称为“经济改革思想史的开创性事件”,它是青年经济工作者“第一次集体发声”。这次会议不仅使一批经济学家脱颖而出,走上舞台,也为八十年代的改革提供了重要的思路,引起中央高层领导的重视。
莫干山会议真正的始作俑者是朱嘉明、刘佑成、黄江南、这四人。当年这四个人都是30多岁,朱嘉明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前身国务院技术经济中心经济师。黄江南是国务院技术经济中心助理研究员。他们俩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工业经济系第一届硕士,此时,刚参加完社科院举办的第一次博士招生考试。是《经济学周报》负责人,中国经济学团体联合会(简称经团联)联络人。刘佑成则是浙江经济研究中心研究人员。
此次会议代表由会议筹备组根据来自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的1300余篇应征论文挑选出来的。在选拔过程中,不讲关系、不讲学历、不讲职称、不讲职业、不讲“名气”,凭论文水平确认代表资格。最后,参加会议的正式代表有124人。
据回忆,莫干山会议的组织分了五个组。第一是领导小组,由各发起单位的组成,他们不负责会议的运作,基本也不参与会议任何决定;第二是大会秘书组,负责会议的组织、议题、讨论、简报、最后报告及各项决定等,任秘书长,成员有朱嘉明、黄江南、徐景安历史新闻大事件、王岐山、王小鲁、周其仁、刘佑成。后来秘书组会议又增加李湘鲁、金观涛,以及各会议分组的部分组长如杨沐、高梁等人;第三是新闻组,由发起新闻单位各出一人组成,中青报记者部主任陆薇薇任组长;第四是会务组,由《经济学周报》和浙江省经济研究中心负责,组长是张连城和蒋晓玲;此外历史新闻大事件,最重要的是学术组,组长和副组长是朱嘉明、黄江南、徐景安,成员为各会议分组组长。
会上没有宣读论文、交换资料、泛泛议论,而是围绕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分若干专题,把探讨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结合起来,拿出解决问题的办法和建议。会议开得热火朝天,有时火药味儿十足。从白天到夜里cctv历史频道,讨论、争论不休。
莫干山会议结束后,在9月15日就完成并上报了七份专题报告。分别是《价格改革的两种思路》、《与价格改革相关的若干问题》、《企业实行自负盈亏应从国营小企业和集体企业起步》、《沿海十四个城市对外开放的若干问题的建议》、《金融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发展和管理股份经济的几个问题》、《粮食购销体制的改革和农村产业结构的变动》。
这些报告,以一种崭新的文风示人,一改动辄引用马列经典的陈词,从问题出发,提出政策建议,得到了高层的重视。此时,市场轨已经开始铺设,价格改革自然成为迫在眉睫的问题。前两年,东欧改革经济学家奥塔锡克来华讲学,就引起并专门讨论过价格问题。这一次,年轻人拿出了比较务实的解决方案。
会议选了几位代表向主管计委和体改委的国务委员张劲夫做了汇报。1984年9月20日,张劲夫批示:“中青年经济工作者讨论会上提出的‘价格改革的两种思路’,极有参考价值。”此《价格改革的两种思路》,是由徐景安执笔完成的报告。
会后,很多人进入了政府体改部门,比如田源成为国家体改委委员。从西北来的年纪最小的参会者张维迎只有24岁,当时在读研究生的最后半年,这年12月,他去体改委报到上班了。会后,还有一批人去江西参加价格改革试点工作。
莫干山会议之后,“中青年”成为了被社会广泛承认的改革时代新名词。莫干山会效应像发射波,一波一波向外扩展。各地政府开始愿意吸纳青年学者的意见,鼓励年轻人冒头。河南省政府组织河南省经济咨询团,邀请莫干山会议中的一些骨干人员成为他们的咨询顾问,于1985年4月在政协礼堂举行聘请仪式,近百位青年经济学家济济一堂,开创了省一级领导和青年经济学家直接沟通对话、直接形成地区发展战略的先河。
有识之士意识到,要把青年经济学家组织起来,为国家的改革开放献计献策,于是体改委组织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随后成立的北京青年经济学会、各地青年经济学会,都是这次会议的直接成果。各省“中青年”对于体制改革的研究也越来越多地介入。
1985年春,法国时装大师,伊夫圣洛朗Yves Saint Laurent 时装展在中国美术馆展出,由于该展览当时与中国国情相差太远,服装理念超前,以至参观人数廖廖,在今天将完全是另一种场面历史新闻大事件。
1989年4月,陕西宝鸡,排队抢购食用油的市民。20世纪80年代末期经济短缺时期, 爆发过许多次抢购风潮。
1987年2月4日,浙江温州苍南县,龙港镇陈定模。陈定模大胆地提出土地有偿使用和梯度移民的设想,使原来的小渔村成为了中国第一座农民城,为中国农村城镇化开辟道路,引起了中央领导和全国各地的关注。
【免责声明】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与和讯网无关。和讯网站对文中陈述、观点判断保持中立,不对所包含内容的准确性、可靠性或完整性提供任何明示或暗示的保证。请读者仅作参考,并请自行承担全部责任历史大事年表高中。
【封面故事】盗火者 1972年,徐庆全 被改革的改革者 曾国藩1870,烈士暮年丁三白伟志 李鸿章1895,穷途末路刘永峰 梁启超1919,被抛弃的勇士李远江 “不合时宜”的年轻人 暗杀时代的青年潮丁三 “五四之子”的后五四时代消失的启蒙者丁三 包在纸里的火 “走向未来”:一群理想者的启蒙之旅韩雨亭 ......
免责声明:本站所有信息均搜集自互联网,并不代表本站观点,本站不对其真实合法性负责。如有信息侵犯了您的权益,请告知,本站将立刻处理。联系QQ:1640731186
 2
2
 0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