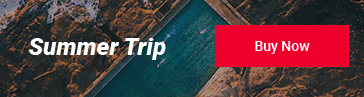历史资料网站凤凰卫视资讯台高清所有观看历史记录历史数据库
信息来源:互联网 发布时间:2023-05-29

还在上世纪二十年代,新闻学在中国就是事实上(de facto)的存在。但从三十年代初开始,试图对其从知识到方法,乃至方的探讨也渐成潮流。为何这门学科刚具雏形,就迅速成为反思对象?这样的潮流承载了怎样的历史意蕴?其中演化 对此后中国新闻学的走向,产生了怎样的影响?这既是本文探讨的问题,也是考察线索。
学术转向往往藉评价学科既往发力。在这方面,发布于1931年10月的《中国新闻学研究会成立宣言》可谓典型。它宣称因为“对过去的新闻学不满足,对现在的新闻业不信任”,所以要对新闻学做“新的开展”(《中国新闻学研究会发表成立宣言:新闻动之新的开展》,1931)。正如相关研究所揭,中国新闻学从一开始,就以“导正”“吾国报业”为主流路径。何以此前此类论著也被看作区隔对象?不妨看看这份宣言的措辞:“‘新闻学’这一名词,在中国学术领域里之被公认,还仅是十数年来的事。在这短促的十数年的过去历史中,它—新闻学—是和中国一切同时的新兴开始建立的其他学术一样,并没有何种具体的成效;甚且是更较其他的学术还要落后地逗留在幼稚状态的初期。虽然在书坊的出版物里,我们是可以找到十种以上的新闻学的著作;但那些因为都是偏于概论的,所以它的功效也就 只能使人除了知道 ‘新闻学’三字以外,就不能供给我们对新闻学更详尽的、理论的与技术的诸般知能之获得。”(《中国新闻学研究会发表成立宣言:新闻动之新的开展》,1931)
不难看出,所以不满足于此前著作,是因为认定它们不能供给“我们”所期待的“理论的与技术的诸般技能”,“偏于概论”是基于此判断的由果归因。那什么才是此时的“我们”所期待的理论与技术?在“我们”那里,怎样的“新闻学”才不算“幼稚”?虽说没有明确列举,宣言也坦率交待:“新闻之发生,是依据于社会生活的需要;社会生活的整体,是基于被压迫的广大的万万千千的社会群众。所以我们除了致力新闻学之科学技术的探究外,我们更将全力致力于以社会主义为根据的科学的新闻学之理论的阐扬”。(《中国新闻学研究会发表成立宣言:新闻动之新的开展》,1931)既然揭出“社会主义”,又认定“广大的”“社会群众”是被压迫的对象,就是以“阶级”作为想象社会的基本立场。而在“十数年前”的徐宝璜、邵飘萍,和其实仅在数年前的戈公振那里,诚然也针砭“吾国报业”,但泛称“吾国”,其实隐含举凡国人,根本上均属一体的意蕴。从这个意义上讲,他们的“国民社会观”与宣言体现的“阶级社会观”的确存在着根本的立场差异。
既然想象社会的路径与结果迥然不同,势必会在至少两个方面导致对“新闻学”的顶层设计存在差异。首先,从目的来看,怎样才算“导正”报业。《新闻学》《中国报学史》等“经典著作”虽说都对报业的“当下”甚为痛惜,却未根本 否定“当下的报业”。因为在“国民社会”的框架下历史资料网站,无论记者、编辑,还是报刊的所有者,都首先是“国民”、“国人”或“公民”。推而广之,这样的本质相同还存在于报人与读者、读者与读者乃至举国人士之间,这就意味着在他们之间未必势同水火。纵使报人乃至国人确实存在种种不足,也只是个体的学识或品格有所不足,完全可以教而知之。因此历史数据库,虽说在什么是“吾国报业”的根本症结上见解不同,但“过去的新闻学”却都认定只要提升报人素养,不仅报业状况肯定改观,国族也会因此受益。譬如徐宝璜期待的教育昌明、国势鼎盛;或如邵飘萍强调的在对外交往中折冲樽俎;再或如戈公振概括的“文学”兴盛则国运昌隆,都是这种“导正”思路的具体展开(朱至刚凤凰卫视资讯台高清,2016:29-56)。但如以“阶级”为基本框架,就意味着必定有部分人在本质上就与多数人的根本利益为敌,而且是以集团形式存在。例如这份宣言就如此总括:“几种所谓大报的经营,在次殖民地的半封建的经济情况下,在买办阶级及统治者的手里,做着被御用的代言者。并向广大的社会群众尽其卑劣的欺骗作用。”(《中国新闻学研究会发表成立宣言:新闻动之新的开展》,1931)就此而言,“对现在的新闻业不信任”不只是对具体运作的不满意,而是伦理层面的根本否定。诸如“技术的落后”“机械设备之不全”“理论的缺乏”“工作人员的腐朽昏庸”“职业饭碗的把握”等等现象都是阶级矛盾必然结果,除非彻底改革所有制度,否则难以有所改观(《中国新闻学研究会发表成立宣言:新闻动之新的开展》,1931)。
其次,“新闻学”应遵循怎样的方法和路径。既然在“过去的新闻学”中,当下的报业所有结构没必要彻底更换(当然,这又是基于对社会制度并不全面否定),要造就理想的报业和报人,也就仅需他们借助专门的“报学”来认知职业(profession),乃至引为“志业”(Beruf)。因此,无论徐宝璜对“教育发达之国”经验的全面介绍、邵飘萍对“记者是为公职”的强调,抑或戈公振对“报业之正轨”的历史叙事,都是以“本行”为主要的经验来源。然而,正如卢卡奇所揭,马克思归纳的“每一个社会中的生产关系都形成一个统一的整体,是历史地了解社会关系的方和钥匙”(马克思,1972:144;卢卡奇,1999:59)。“阶级”不仅是分析事件的框架,还是认识世界的根本尺度。在“阶级社会”的路径下,诸如“族群”“地域”“职业”等其他的群体类型凤凰卫视资讯台高清,即便作为分析工具确有价值,也绝非理解“共同体”(Gemeinschaft)乃至社会的基本架构。从这样的方观照,不仅“新闻学”,任何社会学科如果只以“本行”为知识与方法的来源,而非自觉贯彻“总体化”(Generalization),不管提炼出多少“专业知识”,都只能被视为“庸俗”(vulgar)学术。由此,就不难理解为何宣言会对“过去的新闻学”以“概论式的”一言蔽之。因为在此时的“我们”看来,只有将“社会主义”作为立场,且以“阶级”为方,才有可能使“新闻学”成为“科学”。换句话说,“我们”鉴别“理论和技术”是否“详尽”的首要标准是立场、路径而非数量。既然在方上不科学,那么“过去的新闻学”不止在“过去”,而是永远“不能供给”能被“我们”认可的“理论和技术”。
当然,除了个体思考,学科的立场转向还得以方层面的设定在相当范围被接受为必要条件。但据当事人回忆,“中国新闻学研究会”从未正式开展活动。因 此历史资料网站,这份宣言的价值,主要在作为文本的典型,而非作为节点的关键。但在此前后,“阶级”又的确几近成为中国新闻学的关键词。仅在笔者有限的阅读范围内, 截至1937年7月,至少有19人使用“阶级”作为描述“报刊”或是“报业”的关键词。(可参见纸质版期刊)
从这份材料来看,此时有此倾向的不只左翼中人。譬如谢六逸与“左联”关系一度颇为紧张,成舍我更是报社老板。其实,将“阶级”作为想象社会的尺度而接受,正 是从二十年代初开始,中国知识界的普遍趋势。譬如梁启超在1922年以“有枪”和“无枪”来描叙中国的阶级对立,又在1925年认定相对“无产阶级”,“无业阶级”在当下更具概括力(梁启超,1922:1-6)。虽说当时就受到反驳,却亦可看出“阶级”的话题在这位老辈那里也难以回避(超麟,1925:422)。再如聂云台在1927年提出“明孔孟之道以弭阶级之祸说”,当然逆于时代潮流,也足见在此时的上海,“阶级”的存在,早是公共常识(云台,1927:第231期)。这一在进入20世纪20年代后的兴起,既体现了中国知识界知识来源的“世界化”,也承载了对国族的情怀与思考。先从“世界化”而言。将“阶级”作为认知社会的方,并非马克思主义一家独有。从某种程度上讲,只要承认作为整体的“社会”的确存在,而且“现代性”由此内生,就必然会将考察在“个体”与“社会”之间存在怎样的群体作为中介。而且,在马克思之后,无论对他的学说是否接受,举凡称得上一流的社会科学家(而非仅是社会科学的专家)所有观看历史记录,大多会将“阶级”列为必要的考查维度。再从“国族”来看,虽说“阶级”作为框架极具诠释力度,但未必在任何情境下都与其他尺度不能兼容。尤其是在自认并不在“世界体系”内处于霸权地位的国度,它与“国家”“国族”不仅可成互文,还可以被现实和国际关系不断地应证和强化。这种趋势,在二、三十年代的中国,就体现地相当显著。而且,如果对“资本主义”的理解侧重于行业垄断,对它在中国的蔓延抱有疑惑,也有充分的事实依据。先来看在华的国际资本,据吴寿彭测算,在1928年前后,仅英、日两国对中国工商业的直接投资,就有28亿元左右。约为中国年税收额的4.5倍(吴寿彭,1929:24、52-54)。而在民族资本内部,借助信用杠杆,工商业的生产和销售也出现明显的集中趋势。如据1931年对上海工业调查,当时上海共有1883家工厂,实行公司制的有330家,其中股份有限公司281家,但注册资本分别占到全部资本的71.48%和63.11%(刘佛丁:1983:225)。
既然在“大”及其以后,“国家”“社会”由阶级构成,不同阶级在上的“正当性”(Legitimacy)不尽相同,更几近知识阶层的共识,这自然会影响学术的展开路径(王贵仁历史数据库,2011:90-103;王奇生,2017:30-31)。如在“图书数据库”,可搜到37种图书,书名包含“阶级”,且出版于1937年及以前。又据在“晚清期刊全文数据库”的检索,在1920-1937年间,至少在人文社科8门类的21本学术类期刊中,有78篇论文以此为题名。即便以这样苛刻的标准,仍能由此管窥在此时的中国学界,对“阶级”的关注与引入,是相当普遍的迹象。倘若具象到个案,诸如李景汉对北京城市贫民的家庭情况调查、陈寅恪以“士族阶级”为枢纽梳理中古史、郭沫若提出中国古代社会的阶段划分、吕思勉试图梳理中国阶级制度的整个历史,这些彼时学界的大成就也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了这一趋势。
此时的中国报业,虽说规模较之发达国家还有数量级的差距,却也出现垄断趋势。例如在1936年的北平(人口156万,居全国第2位),《世界日报》《北平晨报》《实报》《新北平报》营业收入(月均7万元)约占全市44家注册报社总和(14.2万元)的一半 。同时的天津(人口106万,居全国第3位),《大公报》《益世报》《庸报》四家的营业收入(月均11.7万元,《大公报》7.3万元),更是占到 全市29家总和(15.5万元)75%。作为对照,在其他民营为主的行当,集中度如此高并不多。诸如时事新报社成批解聘员工(1931年10月)之类事件,就更令人齿冷。在此时的中国,新闻学的研究者大多也是新闻业的从业者。较之其他学科的学人,他们对“资本主义化”感知更为直接,这应该是“宣言”认定“过去的”新闻学“更较其他的学术还要落后地逗留在幼稚状态的初期”的重要理由。
除了“时代”,“世代”所起作用也不容忽视。相关研究已揭出,“中国新闻学”从开始就不是以学习而是以“导正”本国新闻业为取向,当下的“吾国报业” 往往是被批判而非总结的对象(朱至刚,2015:66-79)。进入二十年代后,随着“资本主义”“经营主义”在中国的盛行,这样以批判现状为主要手段来构造学理的路径,不仅没有削弱,反而借助“学科”成形后的知识再生产而延续和强化。譬如谢六逸就因为对中国报业,尤其上海报业的极其不满,嘱托学生以“新闻政策”“上海报纸改革”为学位论文的选题(朱至刚,2016:102-103)。在这种尺度下,与“现在的新闻业”的渊源较浅,反而增加了其言说的正当。也就难怪如袁殊、陶良鹤、郭箴一、张友渔等新一代的学人在构造新的新闻学理时,底气十足。其实,从甲午到抗战爆发,由于国势与国人期待差距巨大,“资历即原罪、新人更正当”的“新陈代谢”,向来是社会心态的重要面相。
当然,要将批评具体化,无论框架抉择,还是措辞展开,都需阐释者主体性的发挥。这些新学人接收和完成教育,大多是在二十年代甚至“大”前后,作为时代的“阶级社会观”,在他们那里浸润更深凤凰卫视资讯台高清。更重要的是,整个“后五四”世代的知识分子,面临的利益分配格局都不容乐观。近年来,胡适、钱玄同、刘半农等人年龄尚轻就得任国立大学教授,常被用作美化彼时知识分子境遇。但且不论他们在同龄人中所占比例,从其产生机制来看,也只是规则剧变中的窗口现象。纵观整个时期,恰恰因为文教领域的生态位被迅速填充,“五四”世代的功名早达才造成了“后五四”世代的机会锐减。虽说彼此岁数相差不大,仅就学术造诣更后出转精, 但如姜亮夫(1902年生,1928年清华国学研究院毕业)、张青莲(1908年生,1936年获柏林大学理学博士)、谭其骧(1911年生,1932年燕大研究生毕业)等同辈中的菁英,却只能以在非顶尖高校(大夏、光华、辅仁)任讲师开始职业生涯。相对其他行当,民营报业提供给新生世代的空间也绝不宽松。据复旦大学新闻学会1934年所做统计,截止1932年夏季,该校新闻专业毕业36人,只有1人被民营报馆录用(徐叔明,《大公报》驻北京记者)(《新闻学期刊》,1934年:166-167)。在这样固化的业界格局面前,无论基于自身际遇,还是对同龄人的物伤其类,在新一代的新闻学人那里,将“阶级”作为方接受,不止是“时代”必然,也是“世代”不平则鸣。毋庸讳言,此时新闻学在中国根基极浅,直到抗战爆发,尚无国立大学将它作为专业设置。新闻学系于1929年出现在复旦,很大程度也是来自学生争取。至于燕大等教会学校,其实和中国社会若即若离。但这反而使“新闻学人”的门槛并不高,为“新人”的批量出现提供了可观空间。据不完全统计,以全面抗战爆发为界,此前10年由国人自著,公开发表的新闻学论著至少有59种,其中论文约189篇,55%左右的作者当时不到25岁。不妨与同期《史语所集刊》对比,到1937年。在该刊发表论文的52位作者中,这个年龄段的仅1人(全汉升)。至于学历,诸如黄天鹏、杜绍文、唐德明、郭箴一、张友渔、袁殊等人,开始发表论著的时候最多刚本科毕业。暂且搁下以规训化后的“现代标准”衡量的深浅粗精,此时中国新闻学的家底浅薄恰恰使方的转向成为潮流更具可能。
与在“学人”中的出现基本同步,“后五四”世代在“报人”中也逐渐占据数量优势。如据《报学季刊》1935年统计,在1934年,也就是“五四”运动15年后,在12省市的从业者中1629人岁数可考,其中不大于33岁1077人,占去66.1%。但在当时,新闻界的上升通道也不宽广,多数从业者只能或长期沉沦下僚,或者转行。也在这一年,有1425人从业年限可考,其中仅330人不少于5年。在这330人中,有182人还在基层岗位,应是从未得到晋升。虽说基层的从业者薪资大多不低凤凰卫视资讯台高清,但在文教行业里,报社的内部差异却明显更大。 在这样的格局下,不难想见,作为动员对象,“后五四” 世代的从业者在整体上会对“新的新闻学”持有怎样的倾向。难怪“中国新闻学研究会”虽说没有真正活动起来,但据《文艺新闻》在1932年4月的说法,闻风而来的会员就有数十人(《中国新闻研究会广征会员》,1932)。
通过前文梳理,应当说已就其内在逻辑和社会动因,大致呈现了以引入“阶级”为共识的“新的新闻学”何以能成为潮流。然而,为何它在后世声名不显?其实,从“学科”的角度并不难理解,因为这场运动虽说声势可观,但并未构造出完整的学理体系。其中人物虽将“阶级”作为方引入,却未能藉此将现象有效地问题化,进而理论化(theoreticalization),更未形成学科共识。既然如此,没能进入“学科”的记忆中心就不足为奇。但为何会出现这样的现象?
如前所述,把“阶级”当做基本尺度并非马克思主义独有,但其他学说,却并非只将生产关系视为想象社会的核心枢纽,因此仅从在生产关系中的位置来定义“阶级”。而且毋庸讳言,无论是否确有自身理路,在马克思之后,却非其信众的顶尖学者,大多还着意与他保持差异。此时的中国恰逢各种络绎而至,知识份子又颇多在未必明其源流,就将它们作为方法乃至方接受。譬如从谢六逸在早稻田大学的专业是经济学来看,他提到的“有闲阶级”可能来自凡勃仑(Thorstein B Veblen)。不管凡勃仑将“有闲阶级”看作社会基本构成是否遵循了他本人试图从思想习惯来梳理制度演变的思路,以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衡量,都毫无疑问是掩饰了真实的社会结构。再如白鹏飞,虽说认为新闻记者大多并无产业,因此“有似于雇佣的劳动者”,但他所使用的概念是“智识阶级”。“智识阶 级”作为观念,虽说内涵不甚清晰,但从语源上来看,与俄罗斯知识份子的精英传统和宗教情结关系匪浅(李桢历史数据库,2016:109-116;别尔嘉耶夫,2004)。至于任白涛,从后来在《综合新闻学》中所有观看历史记录,将马克斯·韦伯和其他绝非同量级的德国学者的观点獭祭成章看来,他在方法和思想上的渊源可谓冗杂。但中国从一战结束到抗战爆发,正处晦明并存的贞元之际。就整个国家而言,虽说对外安全仍受威胁,国内矛盾错综纠葛,也绝非不可救药。知识分子,又出于对国家的责任感,主动寻求各种“主义”济时救世。虽说此后由历史与人民,在各种主义和道路之间,做出了唯一的正确选择。但在当时,对于不仅构成繁复,还是“近代化”的被卷入者的“中国”,各种想象社会的框架却不见得对局部现象全无解释力度。
当然,此时中国知识人对“阶级”和“中国”的认知所有观看历史记录,都既面相丰富,而且相互影响,要将其间关联梳理清楚,既非笔者才识所能,更超出本文探讨主旨。大致勾勒这些结构性的动因后,还是将视线聚焦于这样的思想状况对“新的新闻学”产生的影响。首先,以对“现在的新闻业”,尤其是当下中国新闻业的具体评价为中介,“阶级”观念的差异,自然造成对“过去的新闻学”的态度不尽相同,进而使 “新的新闻学”难以在路径上形成共识。在这方面袁殊的《新闻学论》(1931年)堪称激烈。这篇文章对“新闻”的用法,仍受日文影响,大多是指报刊等媒介。
该文断言“新闻本身的存在价值,在目前阶段的社会里,是属于一切被压迫的民众的。在将来的自由的社会里,是属于全人类的”,同时认定“现代的新闻”,只不过是“直接隶属于资本家的新闻”,“少数资本家的助役机关”,“除了一般社会娱乐外,太半变作野心家所操纵的以大众为对象来开展其欺骗的“仲介机关”(袁殊,1931:1-6)。至于当前的中国报业,“还不过正追随着中国的社会经济之发展,而仍是在“向着资本主义的途中”。不难看出,在他看来,不仅资本家与被压迫的民众根本对立,而且这样的对立在中国已是事实。既然“过去的新闻学”是以 “新闻纸是社会人日常生活里必须的食粮”为展开基点,仅从含糊阶级对立来看,那就是“站在帝国主义、资本主义经济支配下来说”,当然“根本要给它一个完全的否定”(袁殊,1931:1-6)。这样一来,它所包含的具体知识,无论以机关、言论机关、中介机关来界定报刊,还是以“大多数人以最大的兴味”衡量新闻报道,乃至认为“新闻纸是社会人日常生活的必须食粮”,都必须被抛弃。
然而,即便在“中国新闻学研究会”的参与者中,对“过去的新闻学”并非都如此决绝。例如黄天鹏至晚在1929年就用“资本阶级”和“无产阶级”划分报纸,但在此时的他看来,“资本主义”之于“新闻业”作用未必全然负面:“关于搜集贵重之材料,延揽优秀之人才,设备完备之通讯机关,改良之贩卖之分店,与及编辑印刷等等之精进历史数据库,都因有巨额之资本,而臻于美观,凡小资本所不能实现者,至是者能实现。”(黄天鹏凤凰卫视资讯台高清,1991:161)而且在当前的中国,新闻业正是因为“多谋营业之独立,树本身之基础”,才走出“十数年前”的“多汲汲皇皇于谋生存,甚至不自爱而毁其报格。”(黄天鹏,1991:155)因此,虽说他也认为中国新闻业正“托拉斯化”,评判却相当暧昧,“其为利为害者,观乎英美各国之情形,自可瞭然,而不待警言也。”(黄粱梦,1929:116-121)
较之黄天鹏,谢六逸的阶级图景与《新闻学论》相去更远。在“有闲阶级论”的框架下,“非生产性”的特权集团是造成社会不公的主要原因,“企业管理者”虽说不如“工程师集团”理想,但作为社会的主导阶层却不是最差选项(凡勃伦,1981)。因此,在他眼中,中国报业的首要阻碍是“封建余孽”而非其他。他在为《上海报纸改革论》所作序言中,谢六逸还如此铺陈对这类报阀的厌恶:“我只有看着他头上戴着的瓜皮帽顶的红珠子,又注意到他的蓝缎狐皮袍外面罩着一件黑缎的小背心,背心左右两边的口袋里横挂着黄金色的表链,表链上又叮叮当当吊着几个小金磅。”(谢六逸,1931:1-2)再如樊仲云,既不接受“资本主义”为未来取向,更着力痛陈报界当下封建势力之浓厚(樊仲云,1930:52-59)。郭步陶也认定“现在中国的报馆,还在过渡时期。老班的编辑员,还占着重要的地位。老枪的新闻记者,还散布在国内各要地。” (郭步陶,1934:9-10)
黄、谢、樊、郭此时都在复旦大学新闻学系任教,他们的倾向自然会影响学生的判断。例如杜绍文铺陈世界报业发展史后,得出的结论是“故资本帝国主义的毒焰漫天,罪无可逭。但结果文化日进,民智日开,为社会导师的新闻纸,亦随之而鼎盛。此可谓塞翁失马,安知非福,我们痛恨资本帝国主义高压之余,不得不以此自解了。” (杜绍文历史数据库,1931:19)“老唐”(可能即唐克明)将“报纸应不应该托拉斯化”拿来讨论,也许就表明这未见得就是原罪(老唐,1934:155-156)历史资料网站。郭箴一则认定上海报界“在外面,以营利主义之发展,趋于商品化,而内面则以封建之意识为其中心”,“故始造成如此冷酷,幸灾 乐祸之态度,此即其特质。”(郭箴一,1931:85)根据这些论述,认为此时的他们并非马克思主义的同路人,应当不是苛论。
既然此时复旦新闻学系师生虽将“阶级”作为想象社会的基本单位,却未把“资本主义”“资产阶级”视作当下首恶,也就虽以建设“新journalism”为己任,却并不主张将“过去的新闻学”全盘推倒。例如黄天鹏,还在1931年3月就批评自己“总是站在资本主义下探改良报纸,划一新时代作品的“现代新闻学”,即社会主义新闻学,彻底的报纸历史资料网站,到现在还没问世”,但在该年5月出版的《怎样做一个新闻记者》中,他仍将记者描叙为“超社会的自然人”。而且,在介绍该如何研究新闻学的时候,根本没提及阶级立场。
而复旦学子对“过去的新闻学”的态度,在杜绍文的学位论文中可见一斑, “科学化的新闻学理论和人才的建设,科学的新闻学理论的阐明,当在十九世纪的后半期。”(杜绍文,1931:30)既然已经是“科学”,即便时移世易,“按着讲”已有不足,“接着讲”也就足够所有观看历史记录。例如陶良鹤在引述徐宝璜对“新闻”的定义后,补充道“不过近来又加上了二个附件,这种新闻写到新闻纸上来,应该有兴味的,而且同时又合乎伦理的观念。”(陶良鹤,1931:19)所谓“近来”,其实不过强调它们在徐宝璜撰写《新闻学》的时候还不显著。须知复旦大学新闻学系此时就是国内重镇。既然在他们那里,“新的新闻学”更多是对既往学理的延伸和补充,那么对“过去的新闻学”彻底推倒重来势必难以成为学科的共识。
当然,暂时难以形成共识,并不妨碍以一己之力构造起相对完备的学理。然而对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学说,固然“新的新闻学”的诸多参与者没有接受,如袁殊在《新闻学论》中的运用也没入门。如前所述,以“阶级”为想象社会的方并非马克思主义独有。但是,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那里,是在“世界”视野下,将“阶 级”与劳动价值论等其他关键概念融汇为历史唯物主义。从这个意义上讲,历史唯物主义,本身既是辨证的,更是综合的(integriert),如果将其中任何构成从这个有机体系中抽出来单独使用,都是方法意义上的割裂。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就如此批判过格律恩等自诩的“真正的社会主义者”:本来这些主义体系以及评判性的和论战性的主义著作不过是现实运动的表现,而他们却把这些体系与著作同现实运动开来,并且用真正的、绝对的意识即德国哲学的意识的尺度来衡量这个意识,因此他们就离开现实的历史基础而转到思想基础上去,同时又因为他们不知道现实的联系,所以他们也就很容易用“绝对的”或者另外的思想方法虚构出幻想的联系(马克思,恩格斯,1960:536)。
因此,历史唯物主义虽说不拘泥于兰克式的“依据事物真实发生的情况描述它们”(wie es eigentlich gewesen),但自觉将研判放置在具体的总体历史中。譬如对资本主义,马克思不仅声明“我们在理论上假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规律是以 纯粹的形式展开的。实际上始终只存在着近似的情况;但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越是发展,它同以前的经济状态的残余混杂不清的情况越是被消除,这种近似的程度也就越大”,更在《资本论》中绵密梳理资本主义作为社会形态的发生史(马克思,1975:195-196)。返观《新闻学论》,无论对“资本主义”的阐述,还是对“阶级”的使用,恰恰离开了“现实的历史基础”。既然方法上远未成熟,又怎可能在马克思主义的范式下,公允鉴别在“过去的新闻学”,哪些应当保留,哪些需要扬弃,对于“新”的新闻学”,有哪些必须被创设?实际上,越像这样因简单搬用而似乎立场鲜明,在路径上离真正的历史唯物主义越遥远。
相形之下,从《新闻的性质和任务》(1933年)看,张友渔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掌握高出不少。该文开篇揭出“无疑地,新闻是社会的一现象,是社会意识的一表 现。所以说到新闻的性质和任务,也不外是以社会组织为基础应社会的实际需要而产生的东西。人类社会,是采取着阶级对立之形态的人类历史,是演着阶级斗争的进程的”,从上下文看来,这里的“新闻”也是指报刊(张友渔,1933)。紧接着,完整地引用了《党宣言》正文的前六个自然段。这样的引用看似冗长,但与通常只引第一段(“一切从来的社会的历史,是阶级斗争”) 相比,进入语境的深度迥然不同。须知马克思和恩格斯正是基于对阶级关系的具体历史进行梳理,才既精炼地概括出资本主义社会在这方面的特征,更充分阐明这是在历史中“愈加”形成。在现行译本中,最后一句的表述是“但是,我们的时代,资产阶级时代,却有一个特点:它使阶级对立简单化了。整个社会日益为两大敌对的阵营,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其间对历史性和过程性的强调,更是清晰无疑(马克思、恩格斯,2018:1-2)。除了从开始就从这样的深度来把握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学说,在接下来的论述里,张友渔仍在历史脉络中就社会演化剖析新闻事业的性质与功能。这样一来,虽说这篇文章首先是他的专著《日本新闻发达史》所做绪论,但日本新闻业的既往种种,就不仅是被陈述的对象,更是可以从中抽绎出理论的个案。因此,该文所揭出的“新闻最能表现它的性质和任务的时期,是在旧社会和新社会间,正在变革,旧势力和新势力间,正在斗争,以及新社会代替旧社会而成立,但新势力还没有巩固地确立了它的支配地位的时候”,可解释范围自然也不限于日本。
然而,倘若将马克思主义不仅作为信仰,更作为方的准则来看,至少在1930年代初,张友渔虽说在新闻理论(theory about the press)上取得建树,却还没建立起自洽而完备的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理论(theory of the press),因为他还没有对何以无产阶级新闻事业必然具有内在的优越性给出周全阐释。须知在任何具体领域,要将“理论”做到相对完备,都既得对最本体的问题做出明确定义。而且,以此为原点内生展开的解释框架,也能对论域内的其他问题具有相当的诠释能力。在社会科学中,将什么问题认定为最为本体,因此在次序上需要最先解决,更直接影响着学理展开。以新闻学为例,最开始是从“报道”抑或“媒体”“媒介”展开,衍生的知识脉络乃至学科图景也就不尽相同。譬如徐宝璜在《新闻学》中,就是从“新闻纸”说起:“新闻学者,研究新闻纸之各问题而求得一正当解决之学也。”(徐宝璜,1994:1)他所以也要界定“新闻”,只是因为这对于把怎样将“新闻纸”办得“正当”陈述完备必不可少凤凰卫视资讯台高清。
实际上,除邵飘萍以“记者”为本体,诸如徐宝璜、戈公振等“过去的新闻学”的代表,以及黄天鹏、张友渔等“新的新闻学”中人,无论怎样赋予“新闻纸”(或是“报纸”)怎样的界定和期待,都是以媒体为新闻学的考查起点。虽说次序未必等于角度,更未必就是中心。但这样至少在观察的对象上会倾向于以“报刊”或“报业”为范围。如此一来,即便以阶级分析为立场,也很容易走向并非从整个社会的生产关系“观照”,而是依据被提炼出来的“纯粹的形式”去寻找诸多 的行业现象中“寻找”阶级属性。在这样的框架下,要阐明当下的中国报业有“阶级性”,不仅在逻辑上不难,还可举出太多例证,却并不等于在逻辑上阐明了“阶 级性”就是报刊的首要属性。沿着这样的路径,如何能证明在当下的中国,马克思主义新闻学不仅可能完备,而且在自洽上胜过“过去的新闻学”?实际上,其间的 障碍,恰恰就是这种以“新闻纸”为起点,进而视野为其限定的路径事实上放弃了马克思主义作为方的特有之长,就是如卢卡奇看到的:“每一个社会中的生产 关系都形成一个统一的整体’,是历史地了解社会关系的方和钥匙。”(马克思,1958:50;卢卡奇,1999:59)当然,要将历史唯物主义恰如其分地用来考察诸如中国这样的后起国度,进而构造起完备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理论,必须和马克思主义方的另一部分—辩证唯物主义有机结合(朱至刚,2018)。
然而,辩证唯物主义在中国的广为传播和接受,不仅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才初显,更要到延安时期才被发扬光大。就此而言,自然不能责备1933年的张友渔在方上的不甚完备。
仅从在后世记忆,尤其是规制化的“学科”记忆中的显著度而言,抗战前的“新的新闻学”,自然不是辉格史(Whig historiography)意义的关键节点。但即便就学科史而言,上述剖析应能增益我们对中国新闻学演化轨迹之丰富的认知。实际上,倘若不全为专业、领域等定语所规训,其实也不难领会学科史、思想史乃至所有专门史之于历史的总体,本就是其间图景的具体而微。而要具体地在“综合” 中把握“部类”抑或“类型”(type),也许需要以既能映射社会格局,又在各个 “专业”的学术措辞中充分展开的关键观念(thought)作为中介。
从这个意义上讲,也许在思想史和专业史的探讨中,有一个我们在字面上非常熟悉的词汇,作为维度乃至框架的重要性,需要得到充分正视,那就是 “意识形 态”。自然,这里是指在作为学者的马克思等人那里,作为分析尺度的,对象化的ideologie。而且,倘若将“新的新闻学”视作考察精神生产的一个个案,此番探讨 也许还能应证马克思曾阐述的另一个方法准则:“如果物质生产本身不是以它的特殊的历史形式来看,那就不可能理解与它相适应的精神生产的特征以及两种生产的相互作用。”(马克思,1975:296)
免责声明:本站所有信息均搜集自互联网,并不代表本站观点,本站不对其真实合法性负责。如有信息侵犯了您的权益,请告知,本站将立刻处理。联系QQ:1640731186
 2
2
 0
0